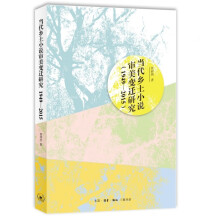《中国现代人生论美学引论》:
在王国维看来,最高之境当为“宏壮之境”。王国维说,美分两种,一种是优美,另一种是宏壮。“要而言之,则前者由一对象之形式,不关于吾人之利害,遂使吾人忘利害之念,而以精神之全力沉浸于此对象之形式中,自然及艺术中普通之美,皆此类也。”①也就是说,能让我们超脱于日常功利之上,仅仅依靠艺术形式来打动我们的,就是优美。而“宏壮”则不同,“后者则由一对象之形式,超乎吾人知力所能驭之范围,或其形式大不利于吾人,而又觉其非人力所能抗,于是吾人保存自己之本能,遂超越乎利害之观念外,而达观其对象之形式,如自然中之高山大川、烈风雷雨,艺术中伟大之宫室、悲惨之雕塑像,历史画、戏曲、小说等皆是也”。②很显然,王国维所谓的优美与宏壮之分,源于康德的优美与崇高之分。康德认为,在优美之外,还有一种审美风格是崇高。崇高与优美的区别在于“自然界的美是建立于对象的形式,而这形式是成立于限制中。与此相反,崇高却是也能在对象的无形式中发见”,③“前者(美)直接在自身携带着一种促进生命的感觉,并且因此能够结合着一种活跃的游戏的想象力的魅力刺激;而后者(崇高的情绪)是一种仅能间接产生的愉快;那就是这样的,它经历着一个瞬间的生命力的阻滞,而立刻继之以生命力的因而更加强烈的喷射,崇高的感觉产生了”。④从王国维和康德的阐述来看,王国维所谓的“宏壮”近似于康德所谓的“崇高”,指那种不借助形式而通过激发起强烈的情感来打动我们的美,比如烈风雷雨、伟大的官室、崇高的情感等。
纵观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唐、宋、元,虽然各种风格的作品均有,但那些“宏壮”的作品,相比那些滥情、小情、娱乐的作品,往往更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如唐诗,“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负有盛名,他们的诗作从文学性来说并非特别高,而是因为他们在当时盛行的奢靡的宫体诗(即王国维所谓的“眩惑”之作)外,力推诗歌的“宏壮”风格。在他们之前,官体诗一直盛行于诗坛,如南朝梁武帝萧衍的《子夜歌》:“恃爱如欲进,含羞未肯前。朱口发艳歌,玉指弄娇弦”,以及唐初上官仪的“瑶笙燕始归,金堂露初唏。风随少女至,虹共美人归”“残红艳粉映帘中,戏蝶流莺聚窗外”等,这些诗歌从文学语言角度讲,可能不输于“初唐四杰”的诗句,但是它们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萧衍、上官仪的官体诗张扬的是奢靡滥情的“眩惑”,而“初唐四杰”的诗句演绎的却是“宏壮”,比如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以及骆宾王的“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都具有一种超越名利、为国为民的豪气。也正因为“初唐四杰”将唐初的诗风由“眩惑”拓向“宏壮”,“唐诗”才不致堕落为文人雅客的玩物,而逐渐发展为唐代的标志性文体。再如宋词。宋词一开始,只是文人雅士消遣的工具.当他们由于各种原因来到青楼的时候,会为那些红颜知己写几首歌词,这就是最初的宋词。柳永是青楼的常客,在歌妓圈中负有盛名,歌妓们相传“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因为这样的原因,柳永在当时“艳”名远播,甚至有“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说法。不过柳永的玩世不恭总算是有了报应,他几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惨遭失败,甚至第二次参加考试之后,得皇上钦点“且去填词”,所以他后来干脆混在女人堆里,天天“奉旨填词”。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