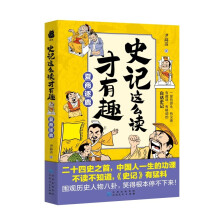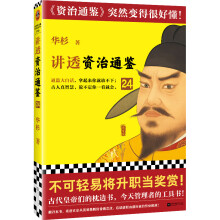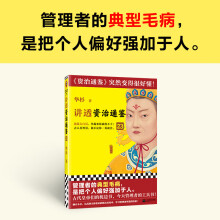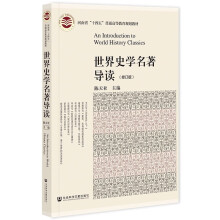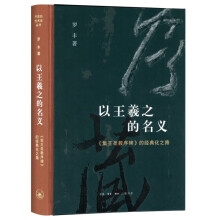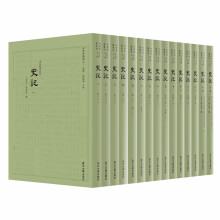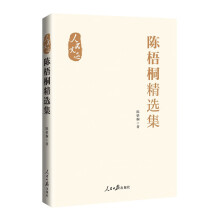摆渡
许是离家多年,总喜欢回忆那些过去久远的东西。坐船摆渡,我有别样情怀。
生我养我的村庄在高邮东乡,名日“司徒潭”。村名含水,可见是水网交错地带。四叉河、五叉河在周边交汇环绕,水乡小镇坐落在绿波中,四面环水,河宽水阔如带,水清幽深似潭。
小时候,河面无桥。村民们进出村子,都是依靠摆渡方便两岸往来。
我与奶奶串门走亲戚,隔三岔五地到与我家隔河而居的邻村大姑妈家做客。走半个小时的田间阡陌小路,到了段东圩堤,遥遥就看见大姑妈家的青砖瓦房了。圩堤两岸,开着白色、黄色或粉红色的无名野花,也有衰败倒伏了的狗尾巴草,泼洒着一幅淡淡郁郁的水乡画卷。
模糊记忆中,有三个渡口过河都可以到大姑妈家。我和奶奶常走段东渡口。乡村的渡口清闲冷落,但摆渡的船家在河岸搭建茅屋,终日守候。渡口有一条简陋的木制摆渡船,招呼一声,摆渡人就过来了。风雨无阻,往返40余米宽的河面,将过河人从此岸送向彼岸,摆一个人一趟渡,只需二分钱。
有时船在对岸泊着,清波粼粼的水面闲荡着一只孤舟。“野渡无人舟自横”,扯着嗓门大声喊“过河哦,过河哦”,摆渡人慢悠悠地把渡船摇过来。等客人上船坐稳,摆渡人就荡桨、退船、掉头,在河边旋半个圈,“吱呀吱呀”划离了岸。静静的河水如碧如茵,清澈见底,木桨点破那水面的碧波,渡船在轻快的流波里荡漾。船行影上,倒影轻动。水浅之处,青绿的水草悠闲地顺水飘摇,小鱼在水草间自在地游戏。翠鸟麻利地掠过水面,给寂寞的河水平添了一分生机。仰坐船头,随船儿轻轻摇摆,恍若置身世外桃源。
大约是常走的原因,一来二去,祖孙俩就和摆渡的船家熟悉了。走累了,走困了,奶奶就把渡口当途中驿站休憩,不再行色匆匆地着急赶路。有时,她和船家的女人聊一阵家长里短,说一些油盐酱醋的琐事,欢声笑语随风一直飘向对岸。家乡人实在,摆渡二分钱,主家也要客气地推让一番,或是塞给我一分钱硬币买糖吃,至今特感温馨亲切。
摆渡充满着乡村的诗情画意,也酝酿过人生悲剧。听老人们说,20世纪60年代,村民们赶村看电影,十一点散场后,最后摆渡过河的是一船年轻人。然而,半夜风起,船翻人亡。回想起来,那是一段撕心裂肺的回忆。
寒暑相易,历尽沧桑的摆渡,在时代变迁中悄然退出了时代的舞台,湮没在了历史的云烟中。在我八岁时,段东渡口搭建了一座石板桥,从那以后,去大姑妈家玩耍做客再也不需要摆渡。而今,故乡实现了“村村通”,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宽敞平坦的公路桥。我从千里之外驾车回乡,在当年的渡口,已经找不到一点儿过去的痕迹,唯滔滔流水依旧。
故乡的摆渡,承载着故乡的父老乡亲,飘摇了一代又一代,摇摆了一年又一年。然而,在我记忆深处,夕阳西下,在河里溅起片片金色粼光,一湾碧水,一叶木舟,好像还在等待我去摆渡而归。
原载《高邮日报》(2010年4月)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