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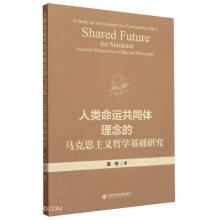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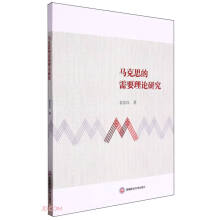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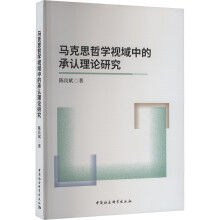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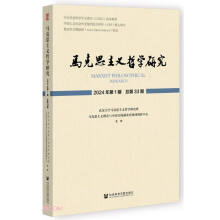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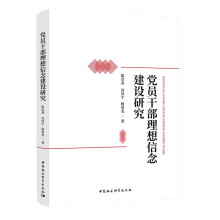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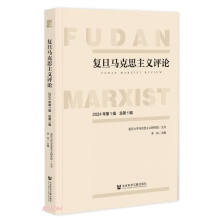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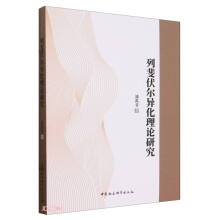
长期以来,对于“马费关系”,国内学界沿袭了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苏联东欧的传统理解模式。这种理解模式虽然比较笼统,可是并没有多大争议。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热潮,大量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学术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其中包含的“人本学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马克思”的观点一度在国内学术界备受热捧,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反而受到一定程度的理论挑战。本书采取了把“马费关系”放入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过程(即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中的研究思路,回到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文本中,回到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当年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尽量还原“马费关系”的历史原像,力争避免国内学界在以往研究上的缺陷。
时至今日,世界依然沉陷在费尔巴哈当年批判的宗教的泥坑里,人们也依然沉陷在马克思当年批判的民族性的泥坑里,因此,这一课题的研究无疑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自
第三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
方法论的全面运用
第一节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论支援背景
早在1842—1843年,作为《莱茵报》编辑的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的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使自己苦恼的疑问,马克思写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但是,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缺乏国民经济学知识的马克思没能完成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批判。为了完成这一批判,马克思开始研究国民经济学。
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理论逻辑要求是马克思进行“国民经济学批判研究”的最初起因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在快要批判完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国家法”部分时,手稿戛然而止。很显然,马克思遇到了麻烦。我们知道,当时的马克思精通法律、哲学、历史和政治等诸多方面的专业知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所有内容,理应都是马克思熟悉的,不至于到写不下去的程度。那么,马克思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呢?我们认为,这个麻烦并不是“市民社会”,而是“政治经济学”。我们知道,法学出身的马克思精通罗马法,而罗马法本身就是以调整市民社会关系为核心的法律体系。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熟悉康德和费希特的法哲学著作,甚至在大学期间还写了一部法哲学著作,因此,马克思根本不可能不了解“市民社会”。但是,此时的马克思确实不大了解政治经济学,尤其是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然而,这恰恰是黑格尔了解的,而且也确实出现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市民社会”一章中。
在《法哲学原理》的“市民社会”一章的第一部分“需要的体系”的开头,黑格尔提到了“政治经济学”。在第189节的“附释”及其接下来的“补充”中,黑格尔对政治经济学做了比较详细的解释。
仔细研读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这些内容,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三个问题:
第一,黑格尔是熟悉在现代世界基础上产生的政治经济学的。在黑格尔看来,作为在现代世界基础上产生的若干门科学的一门,政治经济学就是从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然后按照群众关系和群众运动的质和量的规定性,以及它们的复杂性来阐明这些关系和运动的一门科学。在这里,黑格尔还特意点出了斯密、塞伊和李嘉图三个政治经济学家的名字。由此可见,黑格尔确实是熟悉英国人甚至法国人的政治经济学的。
第二,黑格尔把政治经济学理解为替偶然性找出必然性规律的科学。黑格尔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很有趣的,它可以从中见到思想是怎样从最初摆在它面前的无数个别事实中找出事物简单的原理,即找出在事物中发生作用并调节着事物的理智。黑格尔认为:“某些普遍需要如吃、喝、穿等,它们的得到满足完全系于偶然的情况。土壤有的肥沃些有的贫瘠些;年成的丰谦每岁不同;一个人是勤劳的,另一个人是懒惰的。但是从这样乱纷纷的任性中就产生出普遍规定。这种表面上分散的和混沌的局面是靠自然而然出现的一种必然性来维系的。这里所要发现的这种必然性的东西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这门科学使思想感到荣幸,因为它替一大堆偶然性找到了规律。在这里,一切的联系怎样地起着反作用,各特殊领域怎样地分类并影响别的领域,以及别的领域又怎样促进或阻挠它,这些都是有趣的奇观。这种相互交织的现象,初看令人难以置信,因为看来一切都是听从个人任性摆布的,然而它是最值得注意的;它同太阳系相似,在我们眼前太阳系总是表现出不规则的运动,但是它的规律毕竟是可以认识到的。”
第三,黑格尔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虽然被定位为在现代世界基础上产生的若干门科学的一门,但是,并不局限于对于现代世界的理解,而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很显然,他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并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而是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而且这种政治经济学是用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哲学科学全书纲要》(1827年版)的“导论”中,黑格尔还谈到了英国人对哲学的特别理解。在英国人看来,“那种归功于新近时期的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也特别地叫作哲学,而这是我们通常称之为合理国家经济或近似于理智国家经济的东西”。从黑格尔的说法可以看出,英国人和德国人对于哲学的理解是不同的,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也是不同的。我们认为,虽然黑格尔知道英国人的政治经济学,但是他是按照德国人的方式来理解英国人的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黑格尔理解的政治经济学,并非英国人所指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而是“国民经济学”,具体是指一门系统地研究国家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和手段来管理、影响、限制和安排工业、商业和手工业,从而使人民获得最大福利的科学。实际上,在德国人的眼里,政治经济学就是作为国家学的政治经济学。而在英国经济学家斯密看来,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的科学。很显然,德国人的国民经济学并不同于英国人的政治经济学。对于法学出身的马克思来说,他很有可能是了解德国人的国民经济学的。但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的马克思,对于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是相对陌生的,因此,面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他主要批判了“国家法”部分。因为,马克思当时关注的焦点是政治,而且是德国政治,因此,其他部分对他而言,事实上超出了他的研究兴趣,也超出了他的研究能力。但是,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毕竟是一个整体,马克思所批判的部分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不对相关内容进行批判研究,则无法完成整个批判。于是,马克思接着研究国民经济学,显然是为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的“市民社会”部分做准备。但是,在这里,由于受到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马克思走上了一条与黑格尔理解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国民经济学”)完全不同的国民经济学(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之路。
二、法国、英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直接影响
《莱茵报》时期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的马克思,曾经对刚刚在德国流行起来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保持了谨慎的保留态度,这种谨慎的保留态度一直持续到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之前。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非常意外地谈到了阶级,谈到了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的斗争,谈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即便如此,并没有更多文本证据显示出此时的马克思接受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这种状况在马克思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颠覆性的:马克思接受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并对这种思想进行了哲学和历史的论证。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在自己的这部著作中借鉴了法国、英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我们认为,马克思之所以在“国民经济学批判研究”中要借鉴法国、英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说到底也是一种针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国民经济学批判,这种批判点中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实质,所以在当时的各种批判理论中,这种批判无疑是最为前卫、最为深刻的一种社会批判理论。
对于自己所借鉴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马克思是分层进行描述的:首先,是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其次,是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最后,是魏特林、赫斯和恩格斯的著作。魏特林的著作,马克思没有点出其名称。赫斯的著作,马克思只是点出了其来源。具体是指格▪海尔维格出版的《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文集中发表的赫斯的三篇文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行动的哲学》和《唯一和完全的自由》。恩格斯的著作,马克思直接点出了名称,而且声明自己在《德法年鉴》上已经十分概括地提到过这本著作的要点。
其实,在《巴黎笔记》(马克思在巴黎期间写的九本经济学札记)的第五册中,马克思就曾经对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做了摘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马克思又将之列为“内容丰富而又独创性”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之一。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的“序言”中,马克思更是将之称赞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以上几点,足见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这一著作的重视程度。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已经走在了马克思的前面。这一点并不奇怪。这一时期的恩格斯在英国经商,写过很多关于英国现状的文章,已经足以表明恩格斯对英国状况,特别是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不仅超过了黑格尔,而且也远远地超过了马克思。另外,从同一时期恩格斯所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也可以看出,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是相当熟悉的,这一点也走在了马克思的前面。当然,这一时期的赫斯也非常了解欧洲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因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是在赫斯和恩格斯的影响下关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
三、费尔巴哈的“发现”对马克思“国民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基础性作用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先后两次直接高度评价了费尔巴哈:第一次是在“序言”中,第二次是在“笔记本Ⅲ”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考虑到“序言”是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之后写作完成的,在这里,我们将这两次评价在次序上“颠倒”一下进行分析,以还原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实际过程。
在“笔记本Ⅲ”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第一次对费尔巴哈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评价。马克思首先指出,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做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费尔巴哈的哲学贡献是建立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之上的。当然,这完全符合事实。马克思继而列举了费尔巴哈的三大功绩:
第一,他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应该受到谴责。很显然,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哲学”,指的就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因为,在费尔巴哈看来,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就是神学,就是思辨神学,就是另一种宗教。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克服了黑格尔哲学。当然,这里的“哲学”显然还可以扩展理解为近代哲学,因为“黑格尔哲学是近代哲学的完成”。
第二,他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也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创立了新科学,这种新科学是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这种科学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作为基本原则的。很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并非强调费尔巴哈的自然学贡献,只是表明一种“发生学”的逻辑,最后的落脚点还是人本学。直白地说,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创立的这种新科学就是人的科学。
第三,他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这个评价非常抽象,在理解上确实容易产生分歧。我们认为,这里马克思所说的“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也就是费尔巴哈哲学中的“人”,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也就是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把“人”和“绝对精神”相对立,强调了“人”的重要地位,这本身就是思想史上的伟大功绩。
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这次评价可以看出,马克思只是强调了费尔巴哈在人本学方面的贡献,而对于费尔巴哈在自然学方面的贡献,马克思其实还没有提及。
在“序言”中,马克思再次对费尔巴哈进行高度评价。马克思认为,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和对于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打下的真正的基础。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的著作越不被宣扬,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扎实、深刻、广泛和持久;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从马克思的这个评价不难看出,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完全领会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和自然学,这一点是十分不容易的,因为在《基督教的本质》《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中,费尔巴哈虽然已经明确了“神学就是人本学”,也提出“自然学”的说法,但是,他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明确说出“神学就是人本学和自然学”的观点,因此还导致了当时的很多学者对于费尔巴哈的误解。针对这种误解,费尔巴哈在后来做了解释,补充了“神学就是人本学”的观点,明确说出“神学就是人本学和自然学”的新看法。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居然看到了费尔巴哈想要说出但是暂时没有说出的内容,这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马克思非常清楚费尔巴哈的理论逻辑进路,因此才能够从费尔巴哈已经发表的著作中十分敏锐地捕捉到蛛丝马迹,先于费尔巴哈说出了费尔巴哈的想法。由此可见,在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之间,其实不仅仅是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单向度的影响,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思想“契合”。另外,在这里,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著作看作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肯定了黑格尔,这和第一次单方面地强调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的思路有所不同。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这两次评价,大略来看,意思是差不多的。但仔细研究之后,就会发现这两次评价还有着一个更大的不同:在第一次评价中,马克思实际上只强调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一个方面,即“人”这一个方面,关于“人”的科学其实就是“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在第二次评价中,马克思实际上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并列看待,它们都是“实证的”批判形式。我们认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这两次评价,清楚地表明了此时的马克思不仅领会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和“自然学”,而且已经完全领悟了费尔巴哈的更根本层面上的“发生学观点的批判哲学”,这是极为不容易的。正是凭借着对费尔巴哈哲学的这种精准把握,马克思才能够以之为基础,展开对国民经济学的“实证的”批判之旅。
导言 001
前言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五重否定 023
一、“发生学观点的批判哲学”对思辨哲学的否定 027
二、人本学和自然学对神学的否定 031
三、经验主义对理性主义的否定 046
四、人的自然本质对人的精神本质的否定 052
五、“自然科学”对哲学的否定 061
第一章 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哲学的最初相遇 064
第一节 博士论文写作时期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首次接触 064
一、作为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第一次相遇 065
二、黑格尔哲学史著作: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共同理论出发点 069
三、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在哲学史研究上的比较 072
第二节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初步熟悉 074
一、“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吗? 075
二、“苦恼的疑问”与《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的不期而遇 078
三、《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差异 081
第二章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初次运用 083
第一节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前因后果 085
一、马克思何以选择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进行批判? 085
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文本“缺失”之谜 087
三、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密切关注 093
第二节 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在政治批判中的运用 098
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颠倒过来”方法的运用 098
二、《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继承与发展 103
三、《德法年鉴》时期费尔巴哈对恩格斯的影响 118
第三节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两种思想逻辑 123
一、“政治的”人道主义:马克思“现实人道主义”世界观的第一次阐发 123
二、“政治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政治的”人道主义背后的隐性思想逻辑 126
三、一个没有兑现的“预告”背后的理论困境 128
第三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方法论的全面运用 131
第一节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论支援背景 133
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理论逻辑要求是马克思进行“国民经济学批判研究”的最起因 134
二、法国、英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直接影响 137
三、费尔巴哈的“发现”对马克思“国民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基础性作用 139
第二节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费尔巴哈哲学思想和方法论 143
一、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背后的费尔巴哈“宗教异化”逻辑 143
二、马克思共产主义观点背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视野 145
三、马克思透过费尔巴哈的“眼镜”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 147
第三节 “社会的”人道主义:马克思“现实人道主义”世界观的第二次阐发 150
一、马克思对“人的本质”问题的第一次阐发 151
二、“社会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社会的”人道主义背后的隐性思想逻辑 155
三、“哲学共产主义”: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起源 156
第四章 《神圣家族》时期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最后致敬 165
第一节 《神圣家族》的来龙去脉 167
一、马克思就批判鲍威尔向费尔巴哈征求意见 168
二、《神圣家族》的写作和出版过程 169
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首次合作 172
第二节 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结构秘密的揭露 174
一、马克思对埃德加▪鲍威尔的批判 174
二、马克思对塞利加、布鲁诺▪鲍威尔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 180
三、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上的差异 187
第三节 “历史的”人道主义:马克思“现实人道主义”世界观的第三次阐发 189
一、“历史的”人道主义的最初亮相 189
二、“历史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第一次阐发 193
三、“群众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 199
第五章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整体扬弃 202
第一节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理论支援背景 203
一、《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一次承前启后的思索 204
二、《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次足以致命的攻击 206
三、“布鲁塞尔笔记”:一次研究经济学的强烈印象 211
第二节 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形成 213
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前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演变 213
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实践”概念 215
三、从《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看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218
第三节 “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第二次阐发 224
一、“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对“人本学”和“自然学”的扬弃 224
二、“实践的”认识方法对“感性直观”的认识方法的超越 228
三、人的“社会的”“实践”本质对人的“自然的”“类”本质的颠覆 230
四、“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再定位 237
第六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全面超越 241
第一节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和文本结构 243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 243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结构 247
第二节 “圣麦克斯”章:马克思对施蒂纳的彻底批判 252
一、马克思何以要不厌其烦地抨击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253
二、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第三次阐发 255
三、“圣麦克斯”章:“唯物史观”在多个领域的初步运用 258
第三节 “费尔巴哈”章: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多重正面阐述 263
一、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第一重阐述 266
二、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第二重阐述 271
三、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第三重阐述 276
四、马克思对“人的本质”问题的第三次阐发 278
第四节 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逐渐形成 280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初步批判 282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思想的逐渐厘清 289
第七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的马克思与费尔巴哈 297
第一节 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各自的理论进路 298
一、费尔巴哈的理论进路 299
二、走出费尔巴哈阴影的马克思 301
三、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逆袭 309
第二节 马克思唯物史观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人本学的联系与差别 316
一、马克思唯物史观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人本学的联系 316
二、马克思唯物史观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人本学的差别 319
结束语:卡尔▪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哲学的终结 324
附录一 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学术史对应简表 327
附录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费尔巴哈相关哲学文本对照简表 330
附录三 马克思世界观的五个阶段和四次转变 342
参考文献 353
2016年博士论文后记 364
2019年预出版后记 369
温馨提示:请使用泸西县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