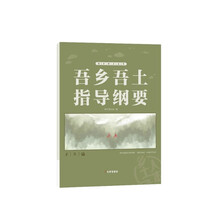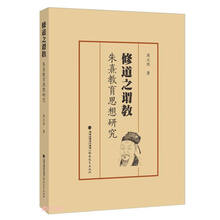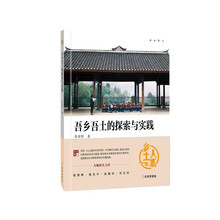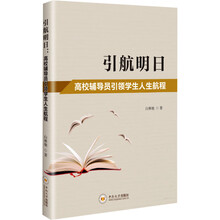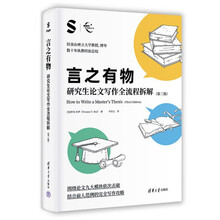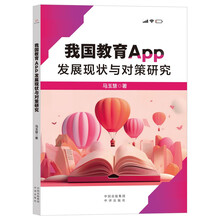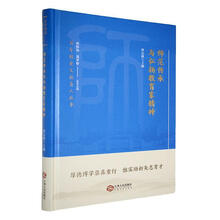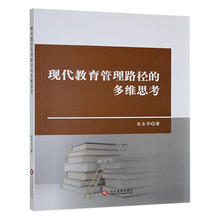《教育发展的个体理性批判:以制致序的逻辑》:
在教育发展理路的历史反思中凸显了制序理路,并对教育制序进行了本体解读之后,就需要进一步回答转型是否具有合理性,即为什么要进行这种转型,教育制序到底能否承担起以它为核心支点来生成人的任务,着实需要一番审察。因为试图以制序公共理性作为寻求“生成真正人”的方式,来解决现存教育中面临的人的“社会性自我”与“个体性自我”之间的矛盾关系问题,初听时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仿佛什么时候进行“社会性自我”的“规训”、什么时候实施“个体性自我”的“自由”,是不能够通过某种“制序”形式来将其“固定化”和“标准化”的,如果“固定化”了,不又走向“僵化极端”了吗?而本书为何提出“制序”型理路呢?本章就是针对这种追问给予理论上的解答,以增强这种理路转型的深刻依据。
在这一章当中,首先从一般性的、总括性的“制序与人的发展”关系的角度给予合理性解答,说明“人的发展”与“制序公共理性”之间的关系;接着深入教育内部从“教育制序与人的生成”关系的角度给予合理性解答。本章是全书的立论根基,关系到教育制序理论能否成立以及教育制序理路的建构等多方面问题,因此要着重笔墨加以论证。
一、教育制序发展理路与人的发展:前提考察
从广义上说,制序是一个与人的发展相生相伴的过程。教育制序发展理路的确立是人类认识论发展的必然选择;是辩证法本质内涵的必然要求;是人的本质规定性的内在要义;是制序本质规定性的内在要求;是交往理论本真要义的直接启示;是人类其他实践领域的间接启示。
(一)人类认识论发展的必然选择
人类思维对实践认识的不断深化选择了“公共理性”。从黑格尔哲学到胡塞尔哲学的哲学演进;从欧洲大陆开启的绝对理性主义到20世纪后半期开始产生的后现代主义的理性演进,都为现代哲学中的一个基本标志——公共哲学的兴起和繁荣奠定了基础。人们扬弃了素朴的“经验主义”;扬弃了“高高在上的绝对理性主义”;扬弃了“怎么都行的后现代无理性”;公共哲学被历史地选择成为时代的思想精髓和理论向导。
公共哲学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一直以来,许多思想家都有类似的寻求“公共理性”或是“公共性”的努力。如近代思想家卢梭有过相近思想的阐述,康德也是如此。康德的“公共理性”和“公共正义”就是为竞争厘定一个基本而普遍的法则。在某种意义上,卢梭和康德为后来的思想家探讨公共性问题提供了两个基本的路向。卢梭试图使人们在各方面都尽量平等,以“公意”克服分立和个别的“私意”与“众意”,为公民社会树立起一个不同于以往宗教的新“神”,将个人利益和欲望、理想汇入一个统一的道德、政治和精神人格,由一种至高精神统摄和引领。康德则强调一种可以面向公众、公开运用的“公共理性”,强调一种普遍然而也是基本的遵守法则。公共哲学被作为一门学科比较明确地提出,大约始于半个世纪前美国著名思想家、政治评论作家沃尔特·李普曼于1956年发表的著作《公共哲学》,其中深刻阐述了如何诉诸公共理性的问题。当代富有影响的思想家也从不同维度对于现代性过程中的公共理性表现出极大关注,如罗尔斯强调社会制度公正优先于个体善;奥斯特罗姆揭示公共事物的治理虽然有不同发展轨迹,但关键取决于更高大层次上的制度合理供给。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些思想家的言论似乎相去甚远,但实际上却殊途同归,不约而同地将注意点聚焦于公共理性及其制度实现形式上。正像福柯启示我们“要跳出要么赞成要么反对这样一个圈套”一样,人类思维对实践认识的结果历史地选择了制序公共理性。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