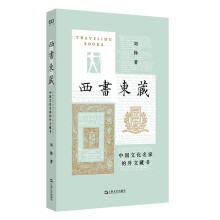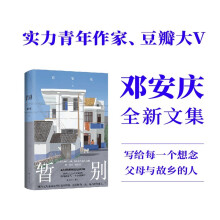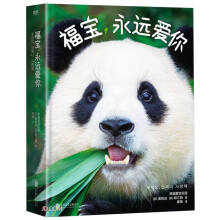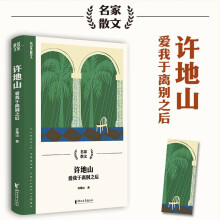《小街连云》:
庙岭山离我家很近,出家门,向东沿中山路步行五分钟即至。我曾是山上的常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读初中,有一要好同学,她家就住在庙岭山的南坡,仅有的一户人家。几间红色的瓦房,在山脚,成为青山的点缀,灿若宝石。一栋二层石头楼,古朴庄重,在绿树丛里隐约可见,是港务局电台。周末时,她常邀我到她家玩。山南有一台阶,向上登十多级,就到一个院子。院子被一棵棵碗口粗的马尾松包围,因为向阳,松树长得特别有生气,地上铺满厚厚的松针,若天然的棕垫。海风从山后浪潮一样涌来,整座山都像在吟唱,声音或高或低,即使是白天,也让人心悸。
一条隧道从山体穿过,隧道名字叫孙家山隧道。那时从陇海铁路终点坐车向西,必然要穿过这个隧道。
我对庙岭山真正的认知已是多年以后,尤其是读过《云台新志》以后。那时,我心里荡起层层波澜,不禁悔意丛生,当年我只需向前向前再向前,只需攀登攀登再攀登,就会成为石刻的见证者之一。可是又有多少人,仅仅因为少迈几步而错过良机,让缕缕悔意萦绕心头呢!在交通极为不便的隋代,海州刺史王谟是令人敬畏的,他乘船顶着猎猎海风,从海浪中颠簸而来。自此,钓鱼台陡峭的石壁上多了“钓鱼矶”三个大字,并且他还赋诗一首:“因巡来到此,瞩海看波流。自兹一度往,何时更回眸。”文人或名士的吟唱,让一座山高大起来。
庙岭山,看似小,其实不小,有名士吟唱着它。
轰轰的炮声,伴随我童年的记忆。1982年6月10日,庙岭新港区第一期煤码头,劈山填海工程全面开工,庙岭山首次大爆破获得成功。
“轰,轰……”庙岭山变瘦了。
“轰,轰……”庙岭山变小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庙岭山旁的过客,我的新家安在庙岭山东侧的荷花街,每周我都要经过庙岭山回娘家。我的娘家在庙岭山西边不远处的二道街。
我们那里人,对庙岭山感受最深的是夏天。炎炎夏日,从中山路由西向东走,只要过了庙岭山头,天地就一下子变了,天更蓝了,云更白了,风一下子变凉了,无形之中像有一台巨型空调,从海上送来凉爽的风,丝绸般地从你身上滑过。大自然就是这般神奇,不由得让自称地球主宰者的人类,常常陷入沉思。
我曾驻足细细地打量,炮声隆隆中的庙岭山。刺耳的炮声过后,一股股昏黄色的烟雾缓慢地升腾,随之飘来的是一股股火药味,山上石头露出狰狞的嘴脸,龇着苍白的獠牙,似在发出怒吼,然后纵身人海,心有不甘。曾经葱郁的山头,早已变成寸草不生的荒山。
一个巨人横空出世,脚下是无数双托起的大手。
一个现代化码头羽翼渐丰,身下是一座曾经生机盎然的青山。
庙岭山碎了,庙岭山沉了,庙岭山不见了!
庙岭港区诞生了,高高耸立的吊车,像巨人的臂膀,在码头一字排开;集装箱,像座座小山,在等待装船走向世界各地……
有一年深秋,连云港当地一诗人,在当地论坛发了一首悼庙岭山的诗,引起许多人的追怀。我想诗人也是看着庙岭山长大的吧!有一天,他恍然明白,身边的这座小山是有历史的,是有文化的,而自己一直无视它的存在。他愧疚了,心痛了,他想弥补,他想听山上石头心跳的声音,想嗅山花吐出的芳香,想吻山间清亮的溪水。他还想像古人一样手持钓竿,在明月朗照下,面对碧海青波,垂钓酣睡在海水里一摇一晃的明月,可是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了。
爱一个人,总是在失去之后,才体会肝肠寸断的滋味。
爱一个地方,总是在面目全非后,才涌起层层叠叠的思念。
庙岭山啊,请原谅无知的小辈,曾对你熟视无睹的漠然吧!
是不是所有的现代化建设,都要以牺牲古代的遗迹作为代价呢?我耳畔响起庙岭山林间的松涛声,它悲壮有力,它雄浑铿锵,它长歌当哭。庙岭山不仅是一座山,还是大自然赐予人间的巨大音箱。世上没有乐师,能奏出它的强音。
有一年,我有幸采访港口集团建港工程师高兆福,他因为发明“爆破挤淤法”而获得国家科技发明奖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什么是爆破挤淤法?最通俗的说法就是利用港口的淤泥造港,这样既可以使海水变清,也不用开山填海。
当时我说,如果这个方法早点发明,也许庙岭山就不用炸了吧?
他说,也许吧!
霎时,一种痛从我心底升起,低头的瞬间,我仿佛看到自己的胸腔,通红一片。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