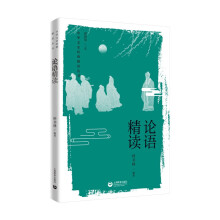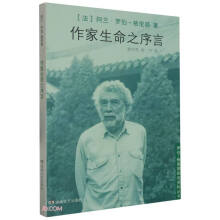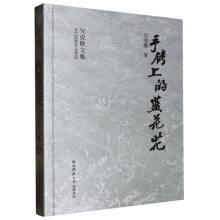《石帆(12)》:
新加坡有根魔术棒
——记新加坡河
◎[新加坡]尤今
夜晚一来,克拉码头就变成了一个华丽而又辉煌的梦,一个让人咋舌的梦。
古色古香的店铺、别具情调的餐馆,一家一家,相依相偎,迤逦而去。密集而灿烂的灯火,像一条金色的火龙,神气活现地划破了寂黑的天幕,延伸到极远极远的地方。夜色啊,妩媚得近乎妖娆。
比克拉码头更像梦的,是那一条静静地卧着的河——新加坡河。
3公里长,万千灯火落在清澈的河面上,铺陈出一片温柔的璀璨,鲜活而又浪漫。它就像是一杯撩人的葡萄酒,不会让你酩酊大醉,但却带给你浪漫的微醺。
这河,不是生而如此的。
它的身世,曲折多变,像是高潮迭起的一部长篇小说。
曾经,它睥睨众生,紧扼着新加坡的经济命脉。
英国殖民者莱佛士于1819年在新加坡河口登陆,高瞻远瞩的他,预见新加坡具有发展转口贸易的经济潜能,于是,把新加坡开设为自由港。豁免进口税,货物价格低廉,河的两岸因此逐渐发展成商贸中心。当时的货物源源不绝地由远洋的大货轮运送而来,在辽阔的海上把货物卸下,转到驳船,再由驳船沿着短小的新加坡河,送到两岸的仓库里。为了应付日益繁忙的贸易活动,在1840年,新加坡河口进行了拓宽工程。到了1860年,栈房、店铺、碾米厂、锯木厂、船厂等各类商号,纷纷林立于河畔。新加坡河口,自此成了重要的货物集散地,世界各地商贾云集,日夜都可以听见经济脉搏跃动的声音——那是一种很强劲、很悦耳的声音。
这个时期的新加坡河,可说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
大家都深情款款地唤它为“母亲河”。
这样一种繁盛的局面,持续了很长、很长的一个时期。
我在1958年随同父母由怡保移居新加坡,极负盛名的新加坡河,当然是我们一家子急欲“瞻仰”的地方。然而,万万没有想到,新加坡河给予我的第一印象,不是“惊艳”,而是“惊愕”。
河面上,是一片熙熙攘攘、汲汲营营的忙碌景象,不计其数的驳船穿梭来去,起货、卸货,吆喝之声不绝于耳。让我惊心的,是那条被人称为“母亲河”的河。我强烈地感觉到,这是一条精力被严重透支的河,它像个任劳任怨的妇人,蓬首垢面地为一家大小的生计默默地做出奉献,大家只注重、只在意它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可它长了皱纹、长了黑斑、患上了心肌疲劳症,却没人注意,也没人关心。
我在画册上看到的泰晤士河(英国)、纳塞河(法国)、莱茵河(德国)、密西西比河(美国),都不是这个样子的啊!它们宁静澄碧,宛如风情万种的贵妇,散发着梦寐的气息,像诗、像画!可为什么这新加坡河却像个苟延残喘的老妪呢?
时光无声流逝,新加坡河,依然日复一日鞠躬尽瘁地操劳着。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码头设备日益现代化,巨大货轮能靠岸起卸货物了,原本往来于新加坡河的驳船已经渐渐无用武之地了。1965年,新加坡独立,经济转型,工业蓬勃发展,新加坡河盛极一时的繁荣便成了明日黄花。
新加坡河在完成了历史使命后,便无可奈何而又无可避免地从人们的视线里淡出了。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道备受冷落的河流,形象糟糕得令人不忍卒读。它邋里邋遢,猥琐不堪。昔日那繁忙的驳运活动使它高度污染而又高度淤塞,“伸手不见五指”的乌黑河面上,污秽的垃圾处处漂浮,黏腻的油渍闪出晦暗的光,更要命的是,让人呕吐的臭气无法遏制地四处飘荡。行经河畔时,人人都掩鼻疾走。当视觉和嗅觉都饱受蹂躏时,大家口出恶言。浑然忘却它过往为人称颂的巨大贡献。
夜半无人私语时,这条苍老多病的河,总难以自抑地发出悲伤的呜咽。
虎落平阳被犬欺,它渐渐成了众人嘲笑的对象。
学校里一名才华满溢的诗人,写了一首诗歌颂它,也许是出于丰富的想象、也许是基于“感恩”的情愫,又或许是要标新立异,诗中用了“潺潺清流”与“芳馥气息”等字眼,他立刻成了众矢之的,攻击与讥讽,有若枪林弹雨,齐齐落在他身上;遍体窟窿的他,被讥为“井底之蛙”“闭门造车”之流,更有人指责他恣意使用夸大的语言来创造“可笑的神话”。
忍辱负重的新加坡河,忍气吞声,默默地流着、不亢不卑地流着……
它在等,静静地等,等待奇迹的发生,等再度成为一则活的神话。它坚持而又固执地相信,它绝对不是“天天在山上盼夫归”那个茫然无措的妻子,它知道,它只不过是暂时“遗失了一只玻璃鞋”的灰姑娘——它清楚地知道,它不会白等。
它的耐心、它的沉着、它的冷静,终于有了回报;它无声的呼唤,也有了回应。
1977年,它等到了它的春天。
当时的总理李光耀,发起了“清河运动”。
“清河?怎么可能?”
百姓都心存疑虑,议论纷纷。这条黑不见底而又臭气冲天的河,明明已经病人膏肓了呀!可坚韧的执政者知道,把梦境化为现实,需要的是愚公移山的决心。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