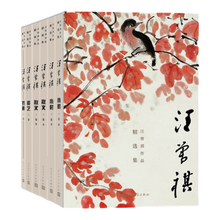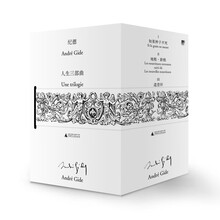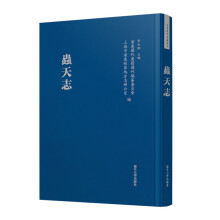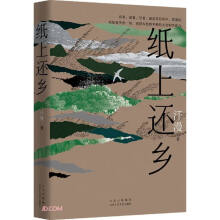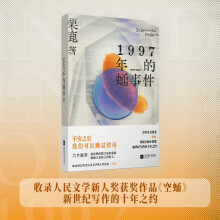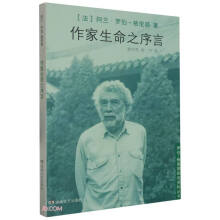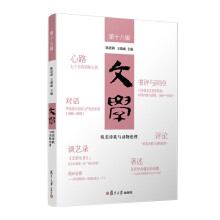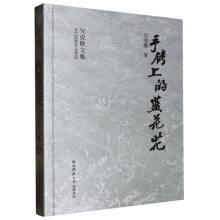《我的名字不叫“等”:戌狗亥猪集》:
第一本:孙犁《芸斋小说》
2019年7月14日,星期日
用孙犁的笔法写孙犁,要简洁。他文字有洁癖。
若干年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永别了,外企》,编辑杨柳大姐说她刚编完《孙犁全集》,三百余万字。我说:“你就等着帮我编全集吧!”
现在才知那是句疯话,人文社是最高殿堂,我或许再无缘进入。
说那句话时对孙犁不甚了解,觉得他是个土作家——写白洋淀的嘛。
今再读孙犁,缘起于《北京晚报》“书乡”张玉瑶文章《后“荷花淀”时期的孙犁》。读完后,巧了,这部《芸斋小说》从书架上探出头,说:“你该好好读读我了吧!”
它,我读过,没觉得什么,那部《白洋淀纪事》也在书堆中藏匿,溜出来,又逃回去了。
《芸斋小说》读一下,放下;再读一下,再放下。不是不忍读完,而是太骨肉连筋,真是太“血腥”了。孙犁像位动刀的外科大夫,而且是极端冷血的那种,把“生命之肉”,一刀一刀地切、片、割,然后,摆放你眼前。
与其说是小说——都不长——不如说是被他写到的那些人物的惨案——很多死于非命。
那个荒唐的年代。
用诗性的文字,写悲剧的故事。
用切割牛排的刀叉,割锯历史苦难。
你不忍卒读,你享受不了,你消化不动。
当年孙犁见人就送一本《芸斋小说》:“请你看看,我的生活,全在这本书里,从中你可以了解我的过去和现在。包括我的思想和感情。”
假如我们将这段话中的“我的”置换成“我们的”——说的是“文革”那代人——似乎更加合适。
第二本:《许君远文集》
2019年7月29日,星期一
《许君远文集》是昨天在天津古文化街的旧书店里不经意间收藏的,因为我从不知道谁是“许君远”。翻看一下,觉得有“民国味儿”,且都是民国时期写的文章,就将其“收留”了:一同打包的,还有解放初期出版的《且介亭杂文》《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侯外庐等著),都是繁体字的书。
我一见繁体字的书就手痒心跳快。
从古文化街出来,上车。出租车司机和我以及同去的两个亲戚讨论起繁体字该不该恢复的话题。
亲戚是台湾生并受早期教育,法国长大和出嫁,她当然说繁体字好。
繁体字的《且介亭杂文》,更有鲁迅的原味,因为原文就是用繁体字写的。
这好比吃“狗不理”,要到原产地天津卫来。
迫不及待阅读《许君远文集》。一翻开,瞥两眼他的行文,就知道他是位才子。果然,北大英文系毕业的,梁遇春、废名的同窗。
他的剧评尤其了得!
从书中得知,赵元任翻译过一部戏——《软体动物》。“软体动物”是指那些“永远不肯动窝”的太太,从许君远的文字中可以想象,那部戏演的过程有多么可乐!
还有,他那篇悼念徐志摩的文章也是极品。
许君远写的文章不多,他60岁就离世了。他是“著名右派”,“右派”帽子本身不至于置人于死地,但他早死些,是和帽子的轻重有关的。
好文章不在多少。一个人一生留下的,在于“成色”。上品文一两篇,其实就够了,就能代表那个人的“文品”。
天津的旧书摊和店铺,我早有光顾。古文化街的这个,已有许久没来。上次在天津买旧书,还是今年“五一”在解放桥上,一位老先生在桥上摆摊,卖的都是旧名著,比如王力的《汉语语音史》。
据知情者说:“现在古文化街也不能随便卖旧书了,你要真想买好的,要早晨五点钟天蒙蒙亮的时候,在那个桥底下,地上摆的都是繁体字老书……”(浓重的天津话)
“哦!”我一边应和着,一边细想回京的上车钟点。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