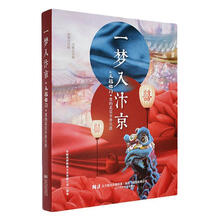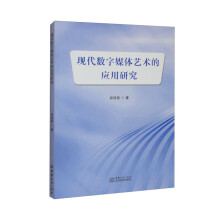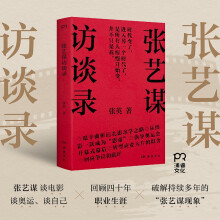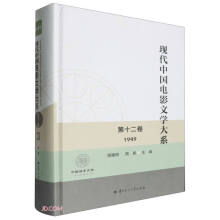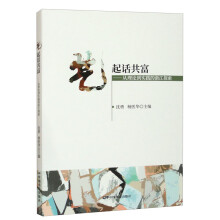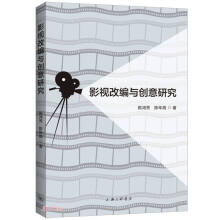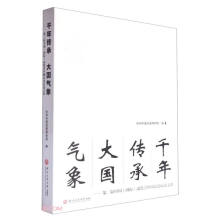《当代电影专题研究》:
《妖猫传》中的日本元素,不仅体现在电影中出现的空海、阿倍仲麻吕、白玲等日本背景的角色上,还体现在电影的出品方角川映画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整个故事的改编中——总体而言,陈凯歌其实拍出了一部“来料加工”(processing)的电影。与此同时,这部电影还是“出口内销两相宜”的。
什么是“来料加工”?在20世纪90年代的制造业中存在一种情况,就是一方将原材料运到另一方处,比如港口等,然后委托其进行外包加工,加工完毕后再将产品运出。《妖猫传》这部电影的制作就是典型的来料加工,日本的出资方委托中国的陈凯歌导演拍摄这个电影作品,其主要的受众群体不只是中国观众,还有日本观众。因此这部电影中许多元素的使用,导向的是满足日本观众的审美诉求这一目的。陈凯歌导演在这部合拍片中,既照顾到了日本的观众,又融人了中国文化,并对其进行表现和传播。所以这部电影作为一部合拍片,是中日文化合作交流的结果。
《妖猫传》改编自日本作家梦枕貘的小说《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原著作者在3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构思《沙门空海》,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并且15次来到中国,花了17年时间才写成。日本人喜欢以中国历史题材进行小说创作,井上靖等就是个中翘楚,梦枕貘也有类似的情意结。值得注意的是,他是在写作著名的《阴阳师》系列的同时创作的《沙门空海》,所以我们很容易在两部小说中发现相似的人物关系。例如,《阴阳师》中的双男主是阴阳师安倍晴明和右近卫中将源博雅,而《沙门空海》中的双男主是日本国派遣的学问僧空海与儒生橘逸势。很明显,这两部作品的人物关系是相互对应的,即一个是带有神秘色彩、懂得巫术的主角,另一个是性格有点憨厚的主角的好友或者助手。这让我们不禁想起了鼎鼎大名的福尔摩斯和华生。陈凯歌在电影《妖猫传》中,用大唐诗人白居易替换了原著中的儒生橘逸势,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改变。这一改变也让电影组成了一对中日之间的跨国搭档,使得《妖猫传》在剧本最重要的人物关系构架上带有“跨国文本”的色彩。
毫无疑问,陈凯歌使用白居易这个符号性的人物有很深的考量。首先,白居易在中国是一个广为人知的诗人,相对于使用儒生橘逸势这个人物,白居易更被中国观众所接受。同时,中国观众一定很难接受由两个都是日本背景的主角来出演一部中国题材的电影。其次,白居易在日本是最广为人知的中国诗人,他的名气超过了李白和杜甫,而这个盛名早在日本平安时代就已经奠定。唐朝是日本人最心向往之的一个朝代,白居易和《长恨歌》也是日本民众最熟悉的作家作品。在这个意义上,陈凯歌使用白居易替换橘逸势可以说同时满足了中日两国观众的需求。
而更重要的“日本元素”还体现在故事中的少年白龙身上。在《妖猫传》中,贵妃杨玉环是一个核心人物,也是所有人目光聚集的焦点,所有见过他的男子都被她的美丽所折服(故而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特别玛丽苏的故事)。白龙是倾慕杨贵妃的众多男子中的一个。在杨贵妃死后,为了守护她,白龙将自己的灵魂寄寓于御猫的身体中,并且在30年后展开了复仇。这是一个为爱痴狂、为爱发疯的人物设定。白龙可以为了杨贵妃死,并且灵魂不灭,因为他要占有杨贵妃,即使那只是一具再也不会苏醒过来的身体。不难发现,这样的人物其实不太像中国文化中会出现的人物。这种决绝的情感非常“日式”。例如,在日本名著《源氏物语》中,被光源氏抛弃的六条妃子,被爱恨纠缠变成怨灵,夜夜作祟害死了源氏正室。还有流传于日本民间的“道成寺钟”传说,女子清姬为了追回失信的爱人变成了蛇,最后将藏身于寺庙大钟里的爱人缠死。陈凯歌对原著的改编,使用了类似的日式情感设定,并将其转译为白龙“少年心”的痴狂、叛逆和执拗。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