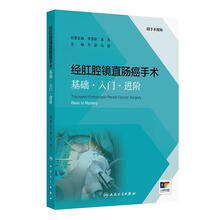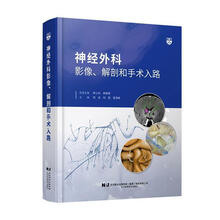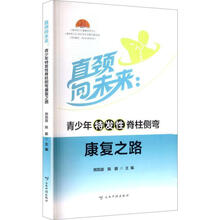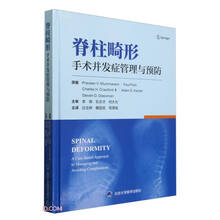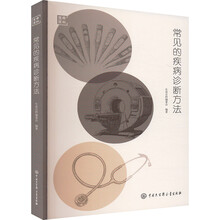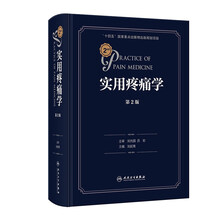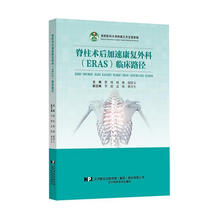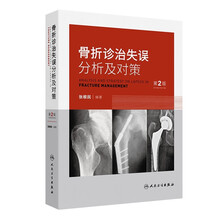第一篇 概论——肤纹学基础
第一章 肤纹研究的简史
皮肤纹理(dermatoglyph)简称肤纹、皮纹。手掌上的嵴线花纹为掌纹,手指上的嵴线花纹为指纹,脚掌上的嵴线花纹为足纹。肤纹包含了指纹(fingerprint)、掌纹(palm)和足纹(sole),是灵长目动物,从低等的原猴类到高等的类人猿,持有的上下(前后)肢掌面的外露表型,是掌面上厚型皮肤的嵴线(ridge,或称嵴纹、嵴)组成的各种类型的花纹。肤纹学(dermatoglyphics)按研究部位分为指纹学、掌纹学、足纹学等;按研究目的细分为非人灵长类肤纹学、人类肤纹学、民族肤纹学、医学肤纹学、司法指纹学等分支学科,在各自领域从不同的方面进行理论和应用研究。肤纹学是以厚型皮肤嵴线花纹为研究对象,以现代统计分析技术和人类其他表型相关分析为研究方法,以发现肤纹生物学信息为研究目的的一门科学。
人类嵴线花纹的研究是一门专门的学科,称为人类肤纹学。人类肤纹学(human dermatoglyphics)以人类厚型皮肤的嵴线构成的花纹为研究对象,以各种现代分析技术为研究方法,以探索人类肤纹理论和应用为研究目的。
嵴线上有丰富的神经末梢和汗腺,对压力、温度等信息的感受更为敏感,具有增加摩擦力的作用,以利于攀缘和紧握工具。在人与大自然抗争的进化史中,肤纹有着重要的作用,故有遗传学家认为:灵长类肤纹的野生型是复杂的斗形纹;简单的弓形纹则是其突变型。肤纹各不相同、终身稳定。
第一节 我国观察与应用肤纹技术的历史
中国是世界指纹观察和应用的发祥地,这一点已得到世界肤纹学界的肯定。我们的祖先观察和应用肤纹的历史已达几千年。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陕西西安东郊浐河东岸半坡村北)出土的陶器,距今已有6000多年,陶器上印有清晰可见的指纹。这些指纹大概是制作时无意印留下来的,但也不能排除有意识作为区别他人产品的标记,或者是作为装饰图案。
在新石器时代的另一处遗址——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出土文物中,亦有陶罐类文物,陶罐上装饰有云雷纹,这种云雷纹是一种有意识的绘画图案(吴山,1975)。
台北故宫博物院铜器展馆展出的青铜器召卣(图1-1-1),是古代的调酒器,满身云雷纹。此召卣为排球样大小,有盖有勺、配件齐全,包浆厚润,品相极好,是西周早期的产物,距今约3000年。
古之云雷纹(图1-1-2)是云纹和雷纹的合称。云纹呈柔和圆形,雷纹呈阳刚方形,大多不做区分或有时难以区分。
图1-1-1 青铜器召卣
满身云雷纹,高29.8cm,宽22.9cm。藏品号:丽七八八故铜1857(台北故宫博物院铜器展馆2006年友情协助)
图1-1-2 铜鼓的装饰纹
右图上二排示云纹,下三排示雷纹(上海闵行区文化馆民族乐器展示厅2006年友情协助)
历史学家郭沫若曾经对3000多年前出现在青铜器上的云雷纹做过描述:“雷纹者,余意盖脱胎于指纹。古者陶器以手制,其上多印有指纹,其后仿刻之而成雷纹也。彝器之古者,多施雷纹,即其脱胎于古陶器之一证。”郭沫若用了两个“脱胎”将青铜器上的雷纹、陶器上的雷纹、制陶者的指纹这三者联系在一起。
美国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中,珍藏着一枚中国古代的泥印,印的正面刻着主人的名字,反面有拇指的印痕,条条阳纹,清晰可辨。世界著名考古学者一致认为,这颗极为珍罕的泥印源于中国古代,距今已有2000~3000年,这颗泥印是指印*古老的实物凭证(Cummins et al,1943;Cummins et al,1976;罗伯特 海因德尔,2008;刘持平 等,2018;沈国文 等,2015)。
秦汉时代(公元前221~公元220年)盛行封泥制。当时的官吏文书大多写在竹简和木牍上,差发时用绳捆缚,在绳端或交叉处封以黏土,盖上印章或指模,作为信验,以防私拆。这种泥封指纹用作个人识别,也代表了信义,还可以用来防止伪造。
1959年,新疆米兰古城出土了一份唐代(公元618~907年)藏文文书(借粟契)。这份契约写在长27.5cm、宽20.5cm棕色、较粗的纸上,藏文为黑色,落款处按有4个红色指印。其中3个已看不出纹线,但有一个能看到纹线,可以肯定为指纹(唐长孺,1994)。
1964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10号墓,发现有唐代贞观元年的《高昌延寿四年(公元六二七年)参军汜显祐遗言文书》(唐长孺,1994),出土的文书已被剪成三张鞋样,一分为三(文书编号分别为10∶38号、10∶41号、10∶42号,图1-1-3)。原著的记载是“本件三片同拆自女鞋,内容密切相关,今故列为一件。在(二)的一、二、三行上方空白处有朱色倒手掌印纹(右手)。在(三)的一、二行上方有朱色手掌印纹(右手)的左半部”。以肤纹学历史的眼光来看:一张有手掌指印,全长16.9cm,除小指部位残缺外,其余部位清晰可见;另一张有半个手掌印,只有拇指和示指,其余部分残缺,指掌分明,视为正规捺印。经鉴定这两张文书上的手印均为右手手印,但不是同一个人的右手手印。这是以手掌包括指纹为信的例证。这份文物在《中华指纹发明史考》(刘持平 等,2018)中有极高的评价,“现存*早的实物资料《高昌延寿四年(公元六二七年)参军汜显祐遗言文书》证明,公元627年指纹技术已普遍在个人遗嘱、私人契约上应用,它有明确纪年,是指掌纹与遗言相结合*早的一份文书,更是迄今为止已知的应用指纹作为诚信方式*早的实物文书,因此其开创的意义非同一般”。这是唐代早期的文书,距今已有近1400年。刘持平还将公认的指纹技术从唐代提前到隋代,彻底解决了近百年来指纹技术发明史上悬而未决的断代问题。在另一本关于指纹历史研究的著作《中国指纹史》(沈国文 等,2015)中,研究者通过东汉郑玄(公元127~200年)对《周礼 地官 司市》的注释及唐代贾公彦对郑玄同样内容的注疏考证后写道:在我国,指纹作为个人标志在契约签署中正式使用,应该是在西汉时期。
图1-1-3 《高昌延寿四年(公元六二七年)参军汜显祐遗言文书》(唐长孺,1994;沈国文 等,2015;刘持平 等,2018)
1964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左憧憙墓出土了8件唐代文书契约,内举钱契4件、举练契2件、买草契和买奴契各1件。这8件契约的立约时间为唐显庆五年(公元660年)至乾封三年(公元668年)。左憧憙生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亡于唐高宗咸亨四年(公元673年)。每张契约上都写着“两和立契,画指为信”或“两和立契,按指为信”,而且每张契约的落款处,当事人、中保人、见证人都在自己的名下画上指印。这些指印都是将手指平放在字纸上,画下示指3条指节纹的距离。古书上所讲的“下手书”,也就是这种画有指节纹距离的文书。具“下手书”的文书实证,还见于出土于阿斯塔那第24号墓地的第28号文书(图1-1-4)(唐长孺,1994),文书上写着“两主和可,获指为信”,并且在各自名下画有指节。
1975年12月,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了12座战国末期至秦代的墓葬,其中第11号墓的墓主喜生于公元前262年,亡于公元前217年,当时喜46岁。在喜的墓中出土了1155枚秦代竹简,定名为“睡虎地秦墓竹简”,或称“云梦秦简”。这一考古工作的重要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法医学的产生、发展和所取得的成就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在云梦秦简中,与法医学关系密切的是《法律答问》和《封诊式》两书,其中尤以后者为甚。《封诊式》的“封”是指查封;“诊”是指诊察、勘验、检验;“式”是指格式和程式。顾名思义,《封诊式》就是一部关于查封与勘验程式的书籍。
《封诊式》全书共25节,包括书题共3010字。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以案例的形式介绍的,但所述案例都没有用真名,而是以甲乙丙丁代表。这说明它不是单纯案例的记录,而是选择极为典型的案例,用以示范或供模仿学习。《封诊式》及云梦秦简中有关法医学内容的记载,反映了我国古代法医学领先于世界各国的辉煌成就。
《封诊式》的《穴盗》一文中记载了一个挖墙洞入民居盗窃的案例。盗窃现场勘查的记录详细规范,记录的内容有报案情况、现场勘查人员的职务和人数、被盗物品的数量和价值、现场访问情况、墙洞大小、房间方位等,是古代办案的范例。在勘查所见的部分写有“内中及穴中外壤上有 (膝)、手迹, 、手各六所”,说明在墙洞内外发现手印和膝盖印痕有六处。《穴盗》的记载表明2000多年前的勘查官员非常重视手印的作用,已把手的印迹作为盗窃案件现场勘查的重要证据。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