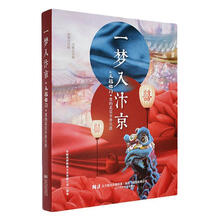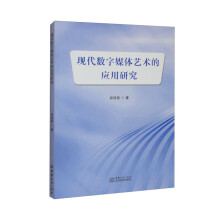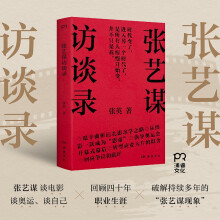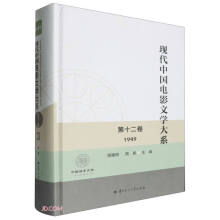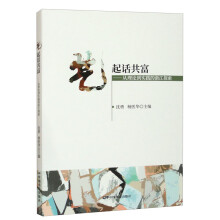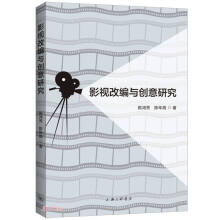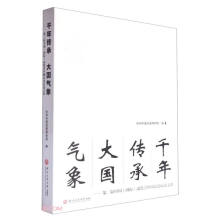《当代华语青春电影研究(1978-2018)》: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影片《街上流行红裙子》中劳模的母亲已毫无遮拦地鄙夷“劳模”无用、不能换来房子。到了90年代,一切神圣的东西皆被抹除了光晕,进入价值交换系统,以交换价值之大小衡量,不能变现的东西就成了空头支票。知识阶层和工人阶级在短暂地共享了80年代前期的中心位置之后,忽然发现自己在新一轮的市场化浪潮中已然濒临边缘化。至80年代末期商品化浪潮席卷神州大地,主流意识形态已不能维系社会的运转。现实的情况是,主流也不知道如何界定自身。而市井之中日益喧嚣的是商品“拜物教”,似乎一切皆有条不紊地走向/预备走向商品化。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大陆青春电影既探索爱情,又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无力感。银幕爱情的无从把握亦是大众对于自身前景之无力把握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不同于80年代大陆青春电影中包裹在宏大叙事之下的无“爱”之爱,90年代青春电影中的爱情叙事已摆脱宏大叙事的框架,沿着80年代后期开辟的、阶层变迁之下的“竞争”路线发展。在90年代转型期焦虑弥漫的社会语境下,对爱情的探索很自然地与阶层重组联结在一起。在90年代第四代导演青春电影中爱情总有一个梦幻性的开端,到结尾往往转向阶层区隔的现实——爱情实难以承担起拯救性的命题。脱离了宏大叙事的爱情在第四代导演的镜头下显得飘忽不定,难以把握,如《北京,你早》和《本命年》。《北京,你早》(1990,张暖忻执导)中“心气高”的漂亮女孩艾红,貌似憧憬爱情,爱情实乃其寻求人生进阶的路径。从同为售票员的王朗,到公交司机邹永强,到高富帅的“留学生”克克,艾红的男友走马灯似的变换——并非她不真心,只是她尚处在爱梦幻的季节(幻想以爱情改变出身)。结果艾红不幸受骗怀孕,克克人间蒸发,然而编导也不忍心让她太过绝望,前两任男友出面教训了假留学生,替她挽回了不算完美的结局。只是“猎艳高手”克克被迫从此安分下来、承担责任,与“心气高”的艾红一起摆地摊、挤公交,很难让人想象“他俩从此幸福地在一起”。同样,《本命年》(1990,谢飞执导)中一开始给了泉子梦幻般憧憬的爱情——他一个刑满释放的青年能够得到漂亮女孩赵雅秋的青睐,成了她的护花使者——短暂易逝,泉子的爱情梦在赵雅秋遇到富商之后烟消云散。
如果说第四代导演眼中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脱离了宏大叙事的爱情是梦幻般的,太轻飘而不能握在手中,同时期第五代导演则大胆地以“都市边缘人”的身份觊觎爱情、俘获爱情,然而终是不知道如何保有爱情,本质上是阶层大洗牌之下日渐边缘的前主流人群对于爱情一厢情愿的意淫。黄建新的《轮回》(1988)、夏钢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1989)以及周晓文的《疯狂的代价》(1988)、《青春无悔》(1991)都是以红色后代自居的“坏男人”与纯情少女的故事。在拜金的时代,没有经济优势的男性试图以“爷们”做派以及厌弃世俗、不循规则的“浪漫主义者”气质(某种程度上也是90年代大众文化想象革命者的气质)赢得爱情。在这些商业类型的青春电影中,境遇悬殊的男女双方总能无阻力地在一起,不过是“好女人倾心坏男人”的老桥段。这类“坏男人”的塑造盗用了革命之遗腹子的想象,然已迥异于“前三十年”的银幕革命英雄:革命血统是他们引以为傲的资本,而革命者的担当与牺牲精神却是他们用来调侃的对象,他们在嘲弄红色话语的过程中标注自己红色后代的贵格。“红色后代”的骄傲不允许他们接受一个女人的救赎,比如,《轮回》中的“顽主”石邑不可思议地赢得了舞蹈演员于晶的芳心,然无法与自己的过去告别,他既拒绝被施予式的爱情,自身又无力从荒诞、虚无的泥沼中拔身而出,只能走向毁灭。此外,诸如《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不务正业的张明与痴情女大学生吴迪,《疯狂的代价》中逃亡者宋泽与不离不弃的美丽女友李晓华,《青春无悔》中脑部受伤的拆迁工人(前战斗英雄)与纯情女护士麦群等,皆是“男性向现代童话故事”中的组合。编导先在自明地赋予这些男性边缘人“丛林式”的强人气质,然而也正是其“丛林式”的野性、拒绝规训(亦拒绝救赎)导致其最终不能被爱情拯救。“拒绝套上笼头的马”最终无法保有爱情,似乎是他们自愿选择放逐,而不是被时代放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香港青春电影中带有匪气的爱情男主角与同时期大陆青春电影中的“坏男人”可谓孪生子。同时期香港青春电影中的爱情频繁出现“浪子”与乖乖女的爱情,如《秋天的童话》(1987)、《阿郎的故事》(1989)、《天若有情》(1990)等,境遇云泥的男女主角,虽能冲破阶层的壁垒为爱勇敢地在一起,然亦是不能善终。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