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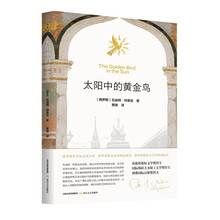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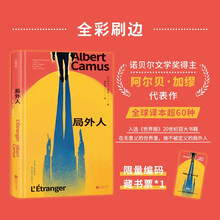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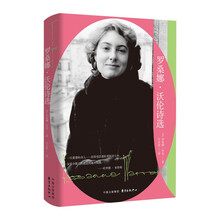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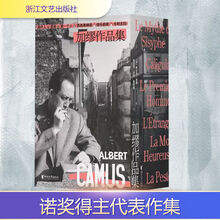

精彩书摘
臭鼬时刻
(给伊丽莎白·毕肖普)
瑙提勒斯岛的隐士
女继承人,仍在她的斯巴达式木屋里过冬;
她的绵羊仍牧放在大海之上。
她的儿子是主教。她的农场管理人
是我们村的首席理事;
她已年老昏花。
渴望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
等级私密性,
她买断朝向她那片海岸的
所有碍眼之物,
任它们倾颓。
季节病了——
我们已失去我们夏日的百万富翁,
他似乎是从一本L.L.比恩精品目录上
跳出来的。他航速九节的帆船
拍卖给了捕龙虾的渔夫。
红狐狸的颜色,覆盖了蓝岭山。
如今,我们的同性恋装潢师
把他的店铺装饰一新,迎接秋天;
他的渔网布满橙色的软木浮漂,
他的补鞋匠的凳子和锥子,也是橙色;
他的活计不挣钱,
他宁愿结婚。
一个昏黑之夜,
我的福特牌都铎爬上山丘的头骨;
我注意到恋爱中的汽车。头灯关掉,
船壳挨着船壳,躺在一起,
市镇的墓地,一级一级地延伸……
我的大脑不太正常。
车载收音机哀鸣,
“爱,哦无忧无虑的爱……”我听到
每个血液细胞里,都有一个病了的灵魂抽泣,
仿佛我的手掐住了它的喉咙……
我自己便是地狱;
此地无人——
只有臭鼬,在月光下
搜寻一口吃食。
它们直着身体,在主街上阔步挺进:
身上是白道道,月光射入了火红的眼,
走在三一教堂的
白垩之燥和尖顶之桅下。
我站在我们的后门
台阶上,呼吸着这浓烈的空气——
一头母鼬,领着一队孩子翻垃圾桶。
它的头像楔子,扎入一杯
酸奶油,垂下它的鸵鸟尾巴,
拒绝害怕。
致联邦死者
(“他们放弃一切,挽救国家。”)
南波士顿的老水族馆
矗立于一片积雪的撒哈拉。破窗钉了木条。
青铜鳕鱼的风向标,已脱落一半鱼鳞。
空水缸里只有风。
曾经,我的鼻子像蜗牛贴住玻璃爬行;
我用手叮叮地敲击,
惊走温顺的鱼群,
鱼鼻上面冒出的泡沫倏然而碎。
我把手收回。常常,我静立叹息,
观看那黑暗的王国里,鱼和爬行动物
倏然而下,植物般生长。去年三月的一个早上,
波士顿市民公园外新立了镀锌的铁丝网,
我把脸贴在上面。笼子里,
恐龙似的黄色蒸汽铲,嗡嗡震颤,
铲起成吨成吨的淤泥乱草,
开挖其地下车库。
停车位野蛮生长,仿佛
波士顿心脏地带供市民娱乐的沙堆。
橙黄色、新教徒南瓜色的脚手架围住的
叮叮叮的州议会大厦,震颤中
俯视挖掘现场,面对
内战时期的肖上校及其圆脸黑人步兵,
在圣高登斯所刻的浮雕里行进,厚木夹板
撑住发颤的浮雕,抵御车库的地震。
他们穿过波士顿,行军俩月之后,
便有一半人员阵亡;
揭幕典礼上,
威廉·詹姆斯几乎听到那些黑人的青铜之息。
他们的碑如一根鱼刺
扎在这座城市的喉咙里。
浮雕里的上校,瘦得
如罗盘针。
他有着一只愤怒的鹪鹩的警惕,
一条灰狗绷紧的温柔;
一有欢乐,他便条件反射似的退缩,
宁可窒息都不愿暴露隐私。
如今,他已出离界限之外。他欣悦于
人类特有的舍生取死的高尚情操——
一旦他率着他的黑人士兵赴死,
便再也无法弯腰。
一千座小镇的新英格兰绿茵上,
都有白色的老教堂冒出,保持着
一种疏阔、真诚的反叛氛围;破损的旗帜
拼织在合众国伟大军队的坟墓上。
抽象的联邦士兵,他们的石雕。
每年都变得更单薄、更年轻——
个个都是蜂腰,拄着滑膛枪
打盹,鬓角都透出沉思……
肖的父亲不要纪念碑,
除了沟渠,
儿子的尸体及其“黑鬼们”的
葬身之所。
沟渠更近了。
这里没有上一场战争的雕像;
在博伊斯顿大街,一张商业化的巨幅照片
把沸腾的广岛安放于
一个莫斯勒保险箱之上,挺过核爆的
“时代之岩”。太空更近了。
当我蜷缩在电视机前,
黑人学童泪水淌干的脸如气球升起。
肖上校
骑在他的泡沫上,
等待
被保佑的破灭。
水族馆消失了。到处都是
鼓鳍前拱的巨型汽车,像鱼;
一种滋了润滑油的
野蛮的奴性滑过。
温馨提示:请使用泸西县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