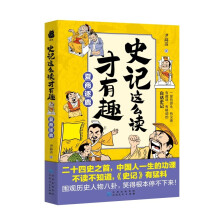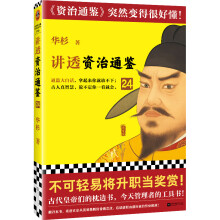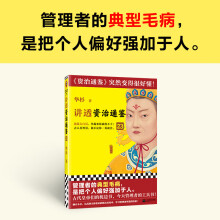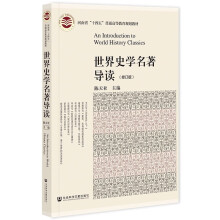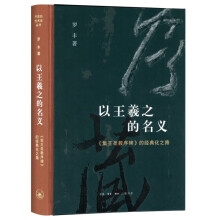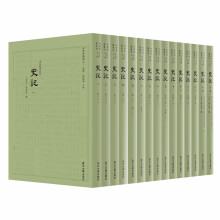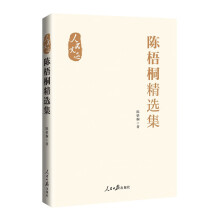一大早,在一声声的鸡鸣声中,西祥庄人又开始了新的一天。
远处,太阳一步步升起来了,渐渐露出了红彤彤的笑脸。此刻,天空和大地都在肃穆中迎接着新一天的到来。
从睡梦中醒来的人们,又开始了新的劳碌。男人们拿起扫帚打扫着大门内外,女人们在收拾清整了住处后,走进了厨房,燃起了一天的第一缕炊烟。窑背烟囱上飘出的那一缕缕灰白的炊烟在天空袅袅上升,最后所有的炊烟都连接起来了,似乎要去向天空的白云倾诉西祥庄人家的光景。远处,不时传来一阵阵狗吠鸡鸣声。
祖父很早就起来了,然后在院子里生着了他的黄泥小火炉,熬上一壶酽茶。茶熬好后,倒进一只瓷杯里,坐在窑洞前的门槛上,一边吹着热气腾腾的茶水,一边望着升起的太阳。茶很浓,它和被火烧得已经变黑的杯子几乎是同一种颜色。楚默然起来后,就跑到祖父跟前去了,爷孙俩坐在那条已经被磨得残破不堪的门槛上,望着不断升高的太阳。这时,太阳笑眯眯地看着西祥庄的一切,也看着一脸懵懂的楚默然。祖父喝了一口茶,抬起头来看了看天空,又看了看楚默然说:“早上凉,快回去把衣裳穿上。”楚默然则说:“爷爷,我不冷。”
在夏日晴好的日子里,楚默然和祖父都是如此开始一天的生活,直到母亲喊他洗脸吃饭。在这个时候,楚默然才知道了祖父人生里的一点一滴。
祖父的老家在陕南栗乡,一个生产板栗和核桃的小山村。然而,那儿的土地物产却不养人。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年代,家里几亩薄田难以养活十几张嘴。作为长子的祖父只好在十六岁的时候含泪辞别亲人外出自谋生路了。
那一天傍晚,当祖父拖着饥饿而又赢弱的身子走到频婆街时,街边一个系着长布围裙的理发匠看着他有气无力的样子,关切地问了一些他的情况后,就领着他去街上一家叫“三水饴铬”的小饭馆吃饭。饭桌上,又累又饿的祖父一下子吃了三碗饴铬。
“小兄弟,你晚上住哪儿啊?”理发匠关切地问。
“大哥,我也不知道。”祖父不好意思地说。
“那这样,你就跟着我去住吧!”理发匠最后说。
祖父跟着理发匠来到了他的家里。理发匠的家,是频婆街南边西沟旁一孔破烂的窑洞。窑洞的对面是一条大沟,沟对面是覆盖着白雪的塬畔,上面长着远远看去像指头一样粗细的树。进到窑里,靠门窗的地方有一个土炕。炕上铺着一张已经发黄的苇席,苇席上面的毛毡上铺着棕色老虎图案的床单,炕旮旯堆着一床被子,上面放着一个被枕得十分油腻的枕头。这时,祖父缓过神来了。他坐在炕边朝窑里不停地打量着,理发匠去外面捡了一笼硬柴,准备烧炕。
炕烧热了,窑里一下变得有了热气。理发匠让祖父一起上炕来坐着说话。当祖父将双脚从那双早已破烂不堪的棉鞋里抽出来时,才发现他的脚已经冻僵了!此刻,他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感激地说:“大哥,谢谢您了!您的救命之恩我终生难忘!”
理发匠一边抽着烟,一边问:“小兄弟,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大哥,我在你们这儿举目无亲,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祖父说。
“唉!现在这么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干什么都不容易啊!”理发匠停下了吧嗒吧嗒抽着的烟说。
“大哥,这儿只有你一个人?你是豳邑县人吗?”祖父转换了一个话题问。
“小兄弟,我的老家在西府的凤鸣县,因为家里弟兄太多,娶不起媳妇,就一个人出来了。”理发匠说。
“大哥,看来我们是同病相怜啊!”祖父说。
“唉,现在这年头,有几个人过得顺心呢?!”理发匠在窗台上的一个烟灰缸里磕了磕烟灰说。
接着,俩人之间一阵沉默。
过了一会儿,祖父终于鼓起勇气对理发匠说:“大哥,你看我能不能留下来给你当徒弟?”
这时,理发匠沉默了。
又过了一会儿,理发匠说:“小兄弟,不是我不想收你,只是理发这个行当有几个人能够看得起呢?!剃头的、唱戏的、呜里哇啦送葬的,都是些让人瞧不起的行当!”
“大哥,我现在就是想谋生活下去,哪还顾得上想这些!”祖父说。
“是啊!可不是人人都能像你这么想。这样吧,小兄弟,既然你能看得起我干的这个行当,那你就留下来吧!”理发匠说。 “谢谢大哥!大哥,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再生父母。”说着,祖父扑通一声,跪在了理发匠的面前。
“使不得!使不得!快起来!快起来!”理发匠把祖父拉了起来,“小兄弟,我还没有来得及问你叫什么名字呢。”
……
P1-4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