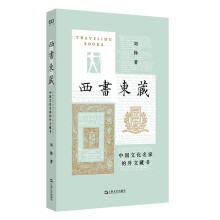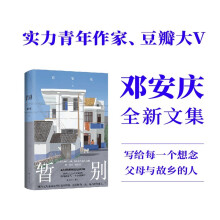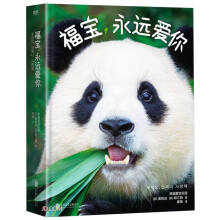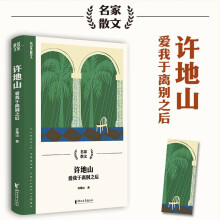土炕
一世为人半世在床。甭问,这话一听就知道是南方人说的。因为南方人都睡床,而北方人大多睡炕。
睡床的南方人比睡炕的北方人总透着那么一点儿精明与高雅,这不是胡说。你看各自的“睡眠心得”就不难得出结论。
睡床的:楼头风景八九月,床下水云千万重;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一窗明月半床书;等等。
睡炕的: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上炕认识娘们儿,下炕认识鞋;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等,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当然了,如果仅凭几句话就分出床、炕高下,那也太过于草率了。难道睡床就形而上、高雅,睡炕就下里巴人、低贱?话可不是这么一说。就拿“床前明月光”来讲,当年李白或许就是躺在土炕上写的。一来,专家论证诗中的床,指的是胡床,也就是马扎儿。二来,西安属北方,从古至今关中、陕北都是睡炕的。
革命圣地延安城里,当年党中央的办公旧址保存完整。一排排窑洞里不见土炕,床具井然。这是因为南方来的领袖们,大多已习惯了“半世在床”,睡不惯土炕。凤凰山下,毛泽东的窑洞里更有土炕上支起一架木床的奇观。在杨家岭朱德的窑洞里,却保留了一盘土炕。导游说:这是考虑到朱老总年岁已高,腿脚不好,单独设计的。
甭管咋说吧,中国革命在延安的窑洞里、木床上,从胜利走向胜利,这应是不争的事实。而在距延安城80公里远的延川县梁家河村的知青窑洞里,一盘普通的土炕正在接受全国各地前来观光学习者的敬仰。
与延安城里那些修旧如旧的旧址不同,这盘土炕已经有了“包浆”——黝黑发亮的木质炕沿,岁月熏染的土墙,锈迹斑斑的油灯等都彰示着:这是“真迹”!
五十多年前,年仅十七岁的青年后生习近平就睡在这个土炕上。
土炕是大地抬起的一部分,睡在炕上就是睡在大地上。接地气,承文脉,通人世。如今,总书记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着中国梦,那些惊世卓然的治国理政思想,可能就是从这铺土炕上萌芽的吧。如此说来,所谓床与炕的高下之分,就有些荒唐了。我是睡炕长大的!我对土炕有着恋母般的情愫。毕竟从母亲的胎盘上下来,就直接躺到土炕上,一躺就是十八年。
说老实话,近年来写乡土文章,我一直躲着这个题材。矫情一点儿说,我有点儿舍不得写它。我觉得这是岁月留给我的一粒糖果,像小时候那样,在实在馋得不行的时候,才偷偷取出,在嘴里含那么一小会儿;之后,赶紧吐出包好,放到时光的衣角深处。像村里人把好东西都藏在炕上;像电影《霸王别姬》里小豆子对小石头说“师兄,别忘了,枕席底下有仨大子儿”;像“黑五类分子”米魁元把派克金笔藏到炕角(参看拙文《村上椿树》);像准备盖房的两口子每晚只有躺在炕上才敢设想未来(参看拙文《“周”起一座房要花多大力气》);像村里的婆姨们把卫生带之类的私密物品洗净包好压到炕席底下,而从不敢晾晒在阳光下……一切贵重的、隐私的、幻想的都藏在炕上。土炕啊,你承载的绝不仅仅是睡眠,还有梦香与梦想!
我是睡炕长大的!但对土炕的搭造不甚了解。
大马村会盘土炕的有几个人,他们有的是泥瓦匠,有的不是。这好像是一门祖传的技术活。有的人专门会盘炕,盘的炕结实耐用,顺烟通畅,一烧就热,省柴省煤。与“一世为人半世在床”相仿,我们村则是一户人家半间是炕。那年月,村里除了赤脚医生的医务室、小学老师宿舍、下乡知识青年宿舍有床以外,全村百分之百都是一炕当家。
这些炕,差不多都是生产队盘造。下此本钱,为的是每年掏取各家的炕灰——这是上等钾肥。由此说来,农民们睡眠时也在种地。
炕一旦盘好就一睡多年。炕席旧了换炕席,炕坯塌了换炕坯,很少见谁家隔三岔五地拆炕重建。炕在,家就在。炕才是大马村人的安身立命之所。
炕规划了家庭秩序。一家人,谁睡在什么位置都是固定的。炕头热,睡老人或是当家人;炕尾凉,睡棒小伙儿。有女孩的,姐姐大了搬到别屋,妹妹或弟弟填补她的位置。很少见一家人今天北头,明天南头地乱睡。汪曾祺有篇写北京人方位感强的文章,说老两口在炕上睡觉,老婆儿嫌老头儿挤着她了,就说“你往南边去点”。若不是位置固定,这深更半夜,黑灯瞎火,迷迷糊糊的,老太太如何准确判断方位?P3-6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