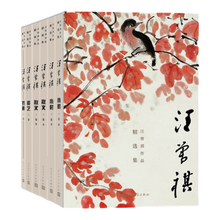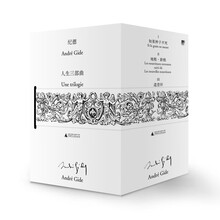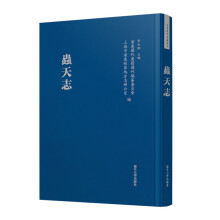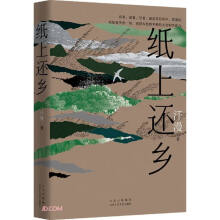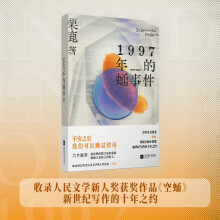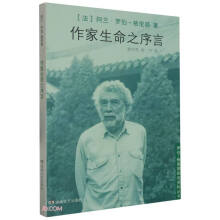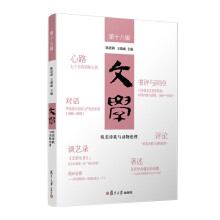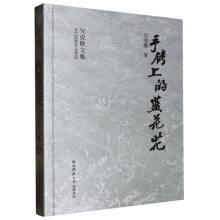鄂南山中的明珠
华尔丹 谌胜蓝
(报告文学)
夜幕降临时分的湖北通城县隽水河畔,89岁的葛旺华在孙子的搀扶下,走在柳堤滨河公园的石板路上。风落到人身上,那是微微高于人体温的温度。明亮的路灯灯光糅着皎皎的月光,这对祖孙渐行渐远,拉长的影子诠释着世间最平凡的生活。
“多亮堂啊!”葛旺华停下了脚步,喃喃道。他们的左边是新建的河堤公园,公园里,人们跟随幸福的节拍在起舞。他们的右边,隔着一条小路是一栋栋老居民楼,并不光鲜的外表承载了这座城市的记忆。路灯下,鲜艳的五星红旗和党旗恰似跳动的火焰。眼前这一抹抹红色突然打在了葛旺华的心上,那种突如其来的温暖紧紧包裹着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轻轻哼唱,不太清透的眼睛慢慢湿润了。他脑海中那些久远的事情渐渐清晰起来,关于他自己的,关于这座城市的。
山窝窝里的小城用上了电
1932年,葛旺华出生在通城县。通城县在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幕阜山北麓,有大小溪流135条,处于“七山一水两分田”的半山半丘陵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通城县是个“三天不下雨,滴水贵如油,一遇洪水遍地横流”的穷地方。当时全县水利设施不足,人民饱受水旱灾害之苦。
1949年6月的一天,通城县县城所在地隽水镇热闹极了。大伙听说镇子上来了个“大家伙”,纷纷停下手里的农活上街看稀奇。大汽车慢悠悠地开进了镇上,车身上还留着战斗中枪弹射击的痕迹,车轱辘上还粘着褐色的泥土。镇上老人说,那是国民党战败溃逃后留下来的车,英国产的,是县里唯一的货车。一些调皮的小孩跟在车后面拍着巴掌嬉笑小跑着。车上装的是一台日产120马力汽油发电机和一台15千瓦发电机。这两个“大家伙”都是用来发电的。那时,17岁的葛旺华和很多人一样,还不知道电是什么。
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如同太阳一般照亮了全中国,也包括这远在千里之外的山窝窝里的小城。随后,通城县政府机关大楼亮起了第一盏电灯。它的光亮温暖着全县人民的心,也点燃了人们对新生活的希望。“这个灯风吹不灭,在晚上跟个太阳一样高高挂在那里,看着亮亮的,心里暖暖的,要是家里也有电灯就好了。”葛旺华第一次见到电灯时,站在那里盯了好久。
1953年,葛旺华是黄袍公社的干事,带着村民修整农田。因为工作出色,1954年6月,葛旺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同事们口中的“小葛同志”。入党宣誓在公社的大礼堂举行,他激情澎湃、声如洪钟,宣誓一结束,就回到村里挖地去了。第二年,在党和当地政府的领导下,通城县人民掀起了深挖塘、广筑堰、固堤防的水利建设热潮。葛旺华成了其中最积极的一员。每天,他带个搪瓷缸子上岗,这一缸子饭菜就解决了他的一日三餐。天气好时,他干脆就睡在坝上。
“这是县里的决定,大家要服从组织安排,有没有主动愿意去电厂工作的同志?”在大家都低着头的时候,葛旺华站了起来,坚定地说:“厂长,我去。”有人在下面小声议论,也有人扯着他的衣角让他别冲动。这是发生在1960年10月18日的一幕。通城县委决定成立专门的电力管理机构:通城县地方国营电厂城关发电厂。电厂厂址就选在了葛旺华工作的农具厂旁边。发电厂人手不足,要从农具厂抽调两人过去。大家对发电厂没什么概念,都不太愿意去。葛旺华心想,自己是一名党员,国家要自己干啥,就干啥。新成立的城关发电厂各项工作都是一片空白。面对崭新的设备和陌生的工作,葛旺华和同事一边磨合一边小心翼翼地“摸着石头过河”。就在这一年,他见证通城县近郊农村150户人家用上了电灯。
两次买电400千瓦的故事
有了电,可是电却不够用,葛旺华想起了通城县两次向外买电400千瓦的事。
第一次发生在1965年。因军工需要,湖北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在北港镇建设湖北长石矿厂。葛旺华和同事们纷纷报名去矿上务工。但是,没电怎么开工?省里的领导为这事来了电厂好多趟。厂长急得没法子。电真是供不应求啊!除了保证政府、学校等重要用户用电,还有百货大楼、农具厂、人民公社综合厂、造纸厂……哪个不要用电?当年,镇上还新建了一个陶瓷厂。厂里几乎所有工序都是半机械化。白天发的电,政府、学校、百货商场用,晚上发的电,居民照明和工厂用。不够用,一些厂子就自备发电机,居民家里也只能限量供应了。这下又新建个矿厂,缺电怎么办?思来想去,上级领导决定向紧邻的湖南临湘县买电200千瓦,并投资27.75万元架设高压线路。这才解了燃眉之急。
第二次买电发生在1970年。通城县矿厂规模越来越大,陶瓷厂向全自动化转型。政府又投资40万元向咸宁市买电200千瓦,并架设崇阳至通城的高压线路。但电力还是紧缺,时供时停。县里48个工矿企业、1万多亩粮田,都“嗷嗷待哺”,等着用电。葛旺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作为一名党员,群众有需求,他不能置身事外啊!
极度缺电现象和通城县内丰富的水电资源形成了强烈对比,引起了一位解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