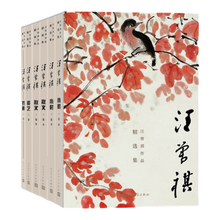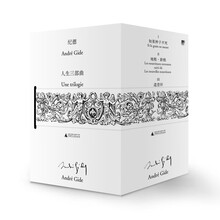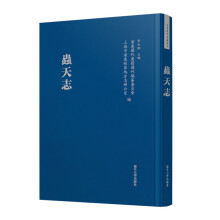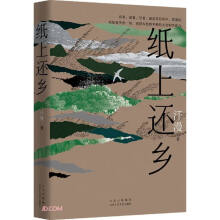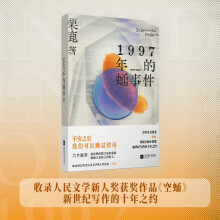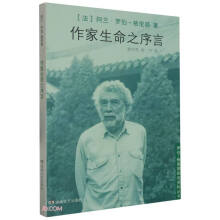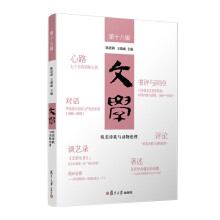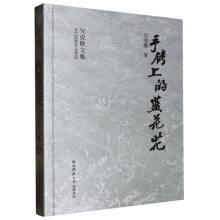北京的深秋,铅灰色的天空下,道路两旁的银杏树已挂满了黄金叶。
他必须在6点前从图书馆赶回酒店,将近一个多小时的路程里,换乘三班公交车,133路市区公交,355路、390路郊区公交;如果错过了酒店员工的晚饭时间,只能饿肚子,或多花几元晚餐费;虽然在他意识深处那么地讨厌金钱。却不得不节省下每一分钱。
歌厅六点半上班,七点钟正式营业。他习惯独处,身上总带便笺纸或者酒水单,习惯把随时的灵感和观察记录下来,有时在公交上,有时在上班时间。也许是回程公交车转过紫竹院围墙,瞥见那个坐在路边拉《二泉映月》的青年,他黧黑的瘦脸,唇上一抹胡楂,一身的灰尘。车已远去,然而二胡悠扬而沧桑的旋律却久久地回荡在他脑海里直到上班。
只是一瞥,他似乎看清了他的经历,于是在吧台上写下了一段句子。七点半来了几帮客人,他们一下子忙碌了起来,所有服务生都在带客,开包厢,送茶水,调音响。他负责吧台工作,忙不过来时,也要帮忙端送盘子。他将背面写字的酒水单本子翻正,放在吧台边上,没有人会在意背面的涂鸦。电话铃响了,许姐接的电话,她倾斜着身子倚靠吧台边上,悠悠地对他说:“松,电话。”然后神秘一笑,将话筒递给他。
芬的声音,给他郁闷的胸肺里注人了春天的氧气。聊了些日常话题,他读的书的内容,她同事间发生的趣事,无论什么话题,都很开心。
“我失业了,去北京找你。”芬的声音陡变凄楚。他吃了一惊,忙说,“北京一点也不好,不要来。”
她嘻嘻地笑,“北京不好,那你干吗还留在北京?”
他笑自己缺乏幽默感。芬的工作,在北京只有本地户口的人才有资格应聘。他自然期待有一天她来北京,但不是现在,也许是某一天,那一天遥远吗?
“许姐叫你到6号包厢。”小周将托盘搁在吧台上,对他说,眼神透着诡谲。小周一直把他当作竞争对手,其实领班的职位对他而言,就是庄子说的臭老鼠肉。在这里工作,只为了生存下来,白天他可以自由地到图书馆看书。
6号包厢里坐了六七个衣着华贵的年轻女士,她们是许姐的姐们,具有那种不能直视的炫目之美。他走到茶几前,双手叠垂,躬身等待吩咐。
“这诗是你写的?”坐在中间的一位紫衫客人,修长的右手指拈着一张酒水单。他认得自己的笔迹,顿时紧张。上班时间写东西——她说的是诗,不是涂鸦——许姐不知要怎么批他,而且还是她的姐们发现的,这说明歌厅的管理不到位。
“除了他,还能有谁,”许姐慵懒地说,“他可是我们的酒店的才子呵。”
他紧握双手,许姐批人时总是正话反说。
“给。”紫衫女士递出一张人民币。
他依旧保持躬身子垂手的姿势,略抬起眼睛直视客人,随时谛听客人的吩咐,这是服务礼仪。
“太少了吧。我出三百。”紫衫女士隔座的一个客人说着,要抢她手上酒水单。
“你少来了,尽跟我抢,”她左手一扬避开,右手从坤包出抄出几张人民币,“这是五百。”她们假意争吵,包厢里尽是她们银铃齐鸣的欢笑声。
许姐说:“快接啊,还不谢谢姐姐。”
他不敢动。许姐把钱塞在他手里,“出去做事吧。”
“别急嘛,陪姐们说说你写的这诗。”那个抢诗的女士说,她轻佻的语气,让他想,应该把小费还回去。
“别捉弄孩子。你去吧。”许姐对他使眼色。他忙抽身离开包厢,转身关上厢门。
“他脸红了。”
“不会是处男吧。”
“哈哈哈……”
“我喜欢。”
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他倍感屈辱。
记得来北京前的那个夜晚,开发区的夜市特别热闹,数日的阴雨天把人们闷坏了,连市区的霓虹灯也闪烁着欢乐。
他们漫步过喧闹的夜市,走到无人的桥头,倚着栏杆,桥下流水潺潺,带着洪水过后的清新水气。连日来暴雨冲刷,混着生活废水与工业污水的臭味,已闻不见了。
“叔叔说,很佩服你。”
他惊奇地看向她。芬的叔叔是他所崇拜的前辈,家里有很多藏书,他们曾秉烛畅谈《红楼梦》。
“你能相信吗?从前叛逆的文艺青年,现在相信命运。”
“你在北京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报考有难度吗?”
“我喜欢挑战。再说,到时候总有办法。”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