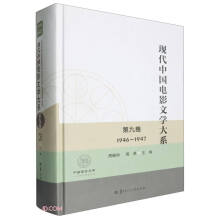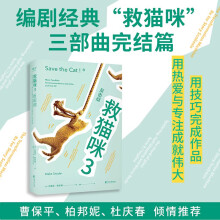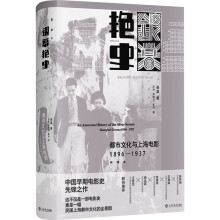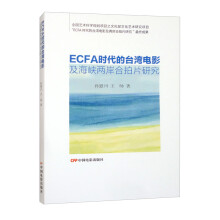《启蒙现代性与中国早期电影的多维透视》:
五、早期侦探片的价值分析
从类型定义上来说,侦探片是一种揭示和暴露犯罪事件或行为的秘密为看点的影片类型,它的“情节一结构”模式以探索某种秘密作为基础,而全部事件都朝着揭示这一秘密的方向进展。它植根于人性深处“窥视”他者的欲望,满足了人们求知探秘的观影心理。早期侦探片作为都市大众文化的一种表达形式,迎合了市民阶层的观众猎奇尚异、寻根究底的审美趣味,是中国早期电影通俗现代性的典型释放。张颐武指出,自古以来中国通俗文艺在审美趣味上存有“尚情”与“尚奇”的两大传统,“基于市民观众的‘情’与‘奇’的表现”是早期中国电影的“另类现代性的主要价值所在”,说它“另类”是因为它提供了与正史所描述的左翼电影与新文学运动“所提供的文化想象不同的文化选择”。如果说早期影史上大量的家庭、婚恋、言情、伦理题材的影片代表了早期电影文化“尚情主义”(艳情、滥情、奇情、哀情等)的一极,那么以武侠、神怪、历史、古装为特色的类型片种则代表了“尚奇主义”(人奇、事奇、情奇、物奇等)的另一极。以揭示与暴露日常生活中难得一见的犯罪行为为看点的、注重情节的曲折和悬念设置的侦探片显然应归入后者的范畴。因此尽管侦探片不是本土文化的~个原生片种,但它在20世纪初期西风东渐、华洋杂处的都市文化的消费语境中,予以适当的嫁接和修正,即可获得相当的接受空间。尽管我国早期侦探片在制片观念与制作水平上与同时期的好莱坞侦探片相比仍然存有差距,但它作为都市大众文化的一种表达形式,满足了一般市民阶层的观影趣味,是中国早期电影通俗现代性的体现,它的“另类现代性”应当给予恰当的“正视”。
首先,与武侠神怪片不同,侦探片展示侦探英雄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沿着蛛丝马迹,展开调查取证,通过抽丝剥茧和理性分析来探究案情,力求显微知著,以理服人。因此,侦探片可以锻炼观众的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开发观众的智力,帮助他们在看似偶然、杂乱的生活表象中建立起深刻的联系。观众在对层层推理的侦查过程的欣赏中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并被激发起求知的欲望,形成了对理性思维和科学实证观的认同。这都让侦探片成为一种既具娱乐价值又有现代科学气息的电影类型。例如拿福尔摩斯这个人物来说,李欧梵指出,他本质上体现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实证精神”“一种基于理性和科学的信念”,这也是广大读者或观众最欣赏该人物的地方。福尔摩斯探案小说描写主人公明察秋毫,沿着蛛丝马迹,运用智慧胆略和侦查技巧,通过严密的推理和谨慎的考证,缉拿真凶,将案情大白于天下,整个过程弘扬了科学实证和理性探索的精神,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对技术现代性的自主掌控。本土早期侦探片同样利用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来设计环节,推动剧情,发挥了传播科学、启迪民智的作用。例如有影迷指出早期“陈查礼”系列电影中的科技元素:“《播音台大血案》中的孙敏,是利用电灯的机纽,《珍珠衫》中刘琼是利用无线电,《隐身盗》中的王竹友是利用电气隐身术,《千里眼》中的严俊是利用电气学中的电波……而‘陈查礼’每逢遇到危险,在一策不展的时候,也往往是以电气上的知识解决了他的危机。”这些人物情节印证了早期侦探片与现代科技的关系,是早期电影对电气、电力、电波等现代物理学知识的运用与想象,彰显了电影艺术紧跟科技潮流的先进性。
其次,本土早期侦探片也提出了依法办案和尊重人权的思想,是五四新文化中的科学与人权并重的现代思想在银幕上的体现。侦探片呈现由侦探来实施侦查和办案,由律师对涉案当事人进行辩护,而不是通过主观臆断和刑讯逼供来判断当事人是否有罪,这促进了国家刑侦司法制度的改良。邹振环指出,福尔摩斯侦探案之类的西方的侦探故事暗示了一种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所忽略的尚理智、重推理、求实据的生活方式,客观上起到了开启民智的社会作用,它“带来了西方社会的一些法制观念和人权思想,这对于习惯读《施公案》《彭公案》《龙图公案》的中国读者来说,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远比人们估计的要高”。林纾在翻译外国侦探小说时就意识到了它对政府的司法制度的改良作用。他说:“近年读海上诸君子所译包探诸案,则大喜,惊赞其用心之仁。果使此书风行,俾朝之司刑谳者,知变计而用律师包探,且广立学堂以育律师包探之材,则人人将求致其名誉,既享名誉,又多得钱,孰者甘为不肖者!下民既免讼师及隶役之患,或重睹明清之天日,则小说之功宁不伟哉!”侦探小说翻译家周桂笙指出:“侦探小说,为我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互市以来。外人伸张治外法权于租界,设立警察,亦有包探名目。然学无专门,徒为狐鼠城社。会审之案,又复瞻徇顾忌,加以时间有限,研究无心。至于内地谳案,动以刑求,暗无天日者,更不必论。如是,复安用侦探之劳其心血哉!至若泰西各国,最尊人权,涉讼者例得请人为辩护,故苟非证据确凿,不能妄入人罪。此侦探学之作用所由广也。而其人又皆深思好学之士,非徒以盗窃充捕投、无赖当公差者所可同日语。”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