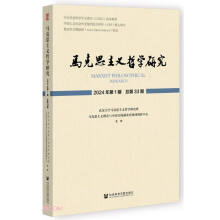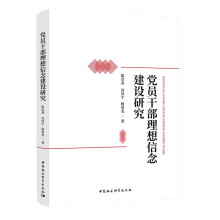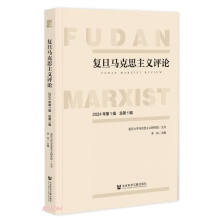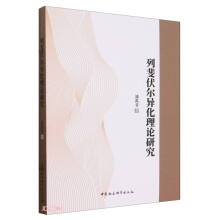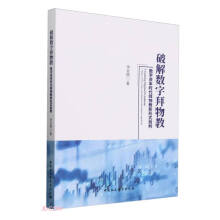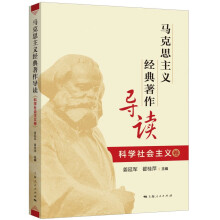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新探:现象学的尝试》:
对认识论定义的理解需要明确其涉及的概念的含义。大多数人可能同意这样的观点:“认识论是关于认识的本质、规律和形式的学说,它以人的认识及其发展作为考察的对象。”这种看法从整体上来看是合适的,但深究起来,该定义中的本质、规律、形式这三个关键词在人们的理解中并不明确,人们对理解这几个关键词的方法也没有明确和统一,这直接导致了对这三个抽象概念的理解会产生歧义,因而致使人们不能真正理解这样的认识论研究所要达到的较为明确的目标。此外,什么是认识也是一个值得探讨和辨析的问题。认识毕竟不同于自然世界的对象,它是对自然世界的对象的认识,如果我把自然世界中的对象称为第一客体,那么,认识作为对象,就只能是第二客体,当第二客体作为认识时,表示的是对第一客体的认识,所以当其作为认识对象时,只能称之为第二客体,因为它是建立在第一客体之上的,它与第一客体肯定是有差别的,所以不能混同起来。对于第一客体,我们可以谈论其具有什么样的本质,但对于第二客体(认识)而言,能否谈论其本质是存疑的,即使用本质这个词去表述对它的研究,其含义也不能等同于自然客体的那种本质。在我的思考中,这两种客体的研究方法、研究目标不应该一开始就混同起来。
研究这些相关概念,本来也属于认识论的任务,但以往对这些概念却很少有明晰的讨论。在哲学研究中,有些人用厚厚的一本著作去研究一个基本概念,这样做固然有其意义,但同时也说明这样的概念已经充满了歧义,含义被人们模糊化了,难以简明扼要地说清楚它,因此才需要重章叠字。试想一下,如果哲学的基本命题需要人们阅读几本著作才能理解,那传播思想的过程中,这样的表达效率也就太低了。如此一来,这些概念可能要被人们逐渐放弃使用了,因为其歧义太多已不适于精确的表达。对于这些基本的概念,利用经验归纳的方法难以形成统一的理解。因为要利用这种方法形成统一的理解,至少需要共同的经验或理解基础。在经验基础上理解这类概念,需要将其与自己真切的认识体验严密地关联起来,并在坚实而明晰的系统化认识中确立其意义,就像通过坐标系描述点的位置或曲线的变化那样,才可能获得准确的理解。经验要素的缺失及构造系统的不严密,都会使得对它的理解和认识变得困难,因而也就难以获得统一的理解,况且,经验是不断变化和扩展的,这才是我们的认识逐渐变得不确定的原因。认识的历史构成使得相关术语充满歧义,但这并非是全然不可解决的困难。我们通过对科学系统的考察,至少可以获得一些解决的思路。诸门科学的概念是在整个系统中呈现的,系统是其认识前提、结构要素、建构原则、理论目标的统一体,是理论的规矩,理论是要素或概念的关系,方法是系统中相对于特定目的而言的要素的结合方式,因此,无论是何种认识论的定义,对它真正有效的理解都需要可行的方法和对与其相应的理论系统的认识才能完成。
我们接着恩格斯的话继续讨论。虽然通晓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是认识论研究的必要工作,但我们不可能通过总结所有的认识成果及认识论研究的成果就能形成科学化的认识论概念。这种总结和概括有时候是必要的,但并不意味着就能形成有利于我们展开研究的总概念,它仅仅意味着我们要熟悉一门科学产生之前的历史,以避免忽视过去的意义,避免做重复的探索,避免过去的差错,甚至希望能够获得一些思路。不同类型的认识论有不同的认识目标和前提,它的问题和概念产生的起点不一样,研究方法也不一样,由于这些不同之处,对其观点的总结和概括就难以真正形成统一的认识论概念。即使以这样的方式形成了相应的总概念,它也只能作为研究的提示与参考,需要在研究进程中对它进行分析和考察,需要究查它是否能满足我们的认识需求。
但在研究之前,我们总会对概念有所规定,这就形成了做法上的矛盾,即定义所面临的不合适的境遇与我们不得不采取这种做法之间的矛盾。然而正是这种做法产生的矛盾,才使我们看到了在主观上借以克服它从而使认识得以进步的契机。通过对它的克服,恰恰可以推进我们的研究,而不是由于碰到矛盾和困难而止步不前。如果在认识中没有矛盾,就要去发现矛盾,或“制造”矛盾,使双方的实质在对立中能够彼此被激发出来,然后才能在矛盾双方的对立中看到问题的实质,从而才能真正地推进认识。因此,自相矛盾并不可怕,可怕之处不在于分析和解决矛盾时遇到的困难,而在于抛弃矛盾。
因此,我们需要在系统地开展研究时首先确立一个定义,然后展开对它的分析及研究,以逐步断定这样的规定是否有利于我们的研究,而后谋求将其修改和变更为有利于我们开展研究的较为合适的定义。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不断在含义的对立中确立术语的含义。尤其对于抽象的概念或术语而言,由于抽象可以是反向的,所以必然存在与其对立的含义,如果使含义处于对立的状态中,就能使我们更清楚地明白这些概念的含义。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