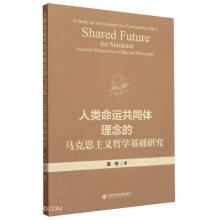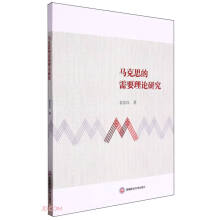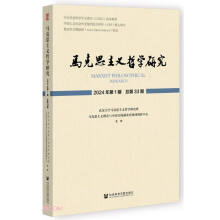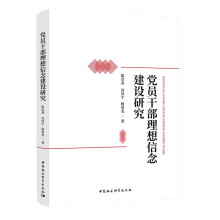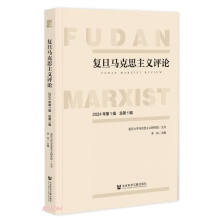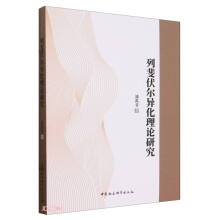后面海德格尔在论述伦理学时指出,正是对存在之思的遗忘,正是在技术性之思中,才出现了以伦理作为行动的外在规定。这就是说,虽然萨特想以存在先于本质来反对传统哲学中技术性思维,但其思维本身仍然没有跳出这一思考框架。其次,海德格尔批评了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这个命题。由于“存在”规定着人的本质,这种本质关系由思完成,存在、本质与思就处于一种同构关系中,那么存在先于本质这个说法就不再具有特别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两者对“存在”的理解决然不同。海德格尔所理解的“存在”不是存在者意义上的东西,而是构成人类生存的本真规定的存在。而萨特的“存在”实际上是一种人的生存意义上的“存在”,即人在那儿这是一个无法否定的事实,这个存在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生存,而在海德格尔看来,生存本质上是由存在规定的。海德格尔认为,如果从萨特所说的“存在”出发,思就仍然停留在“技术”性的意义中,因为“思”是从存在者出发的。海德格尔认为,“思的严格处在于,说总纯粹地保持在存在的基本成分中并让说的形形色色的各度中的简单的东西贯串全局”①。如果存在先于本质这个命题是成问题的,那么,奠基于这个命题之上的“人道主义”之说是否还有必要呢?在萨特那里,为了批驳反对者,他将自己的学说称为人道主义,而且认为只有存在主义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海德格尔对此提出了质疑。
首先,海德格尔对“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进行了分析。思是对存在之思,那么构成思的基本成分的就是“思从其中出发才能成其为思的东西”,这个基本成分就是能力;但思是听从存在而又属于存在的东西,思只有在存在之中,才能成其为思。当思存在时,存在已听命地主宰其本质了。因此,当思成其为本质时,这种能力的真正的本质就不仅能做出这件事或那件事,而且能让一个东西在它的来历中成其本质,也就是说让它存在。由于存在之思总是历史性地发生着,也就不可能出现超越于历史性之上的体系哲学,或者说思不可能是“主义”式的。只有当思偏离其基本成分时,才会出现像“主义”这样的名称,而这个名称正是公众需要的。“人们固然久已不信什么‘主义’了。公众意见的市场总需求新的‘主义’。人们又总是愿意供此需求。”②在对“主义”的需求中,思的基本成分即“能力”被理解为与现实性相对应的可能性,“这种解释把存在解释为现实与潜能,而人们又把这种区别和存在与本质的区别等同起来”③,这是传统形而上学关于存在的解释。实际上,萨特对“存在”与思的理解,正是海德格尔所批评的上述解释模式。当思从基本成分中偏离出来,哲学就把思作为一种技术加以弥补,造成了哲学与其他学科的竞赛,“在从事于此的竞赛中哲学就公开地献身为一种……主义并力图取胜”。很显然,这里海德格尔没有点萨特的名,但实际上,他将萨特当作传统形而上学的解释者加以批评。
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结合萨特文章的意图,对“主义”的需求进行了更深一步的分析。萨特写这篇文章时指出,如果存在先于本质,那么过去从先在本质出发的一切学说都不能作为行动的标准,人必须在自己的行为中成为人本身。萨特这里是想以一种“个体”式的生存代替过去由先验本质“克隆”出来的公众生存。对此,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当萨特将这种生存当作一种存在主义方式时,像“主义”这样的名称,其“统治地位是来自独特的公众的专政,而尤其在新时代是如此”①。这就是说,萨特的本意是想逃出公众之役,但由于这种逃避只是一种否定,这种抽象的否定只能靠从公众事物中抽身回来养活自身,因此,萨特的私人生存就违反了自己的意愿而确证了为公众之役的情况。这种理解方式,是传统形而上学从存在者与对象着眼的必然。在对象化过程中,思成为达到对象的工具,语言也成为工具,“把一切事物对象化的情形就是一切事物对一切人都是在忽视任何界限的情况下同形式地可接近”②。这时,一切人的意见就非常重要,公众的专政就在所难免。在传统形而上学基础上谈人道主义,这就是一种新的公众之役。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深刻的洞察。
就学理而言,海德格尔的思考无疑是深刻的。但这里的深层问题是,海德格尔与萨特的努力形成了对比:萨特想将人的自由与历史的限制结合起来,这倒具有现实的意义;而从对存在之思出发时,对人类历史内在分析就不再重要了,海德关于人性的思考,倒是真的陷入了一种存在的想象中,这在下面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