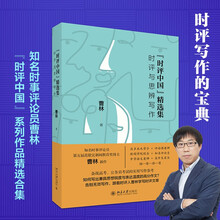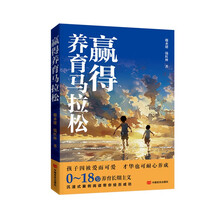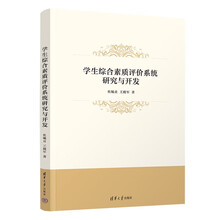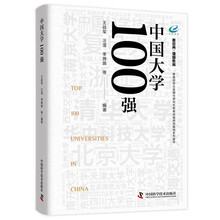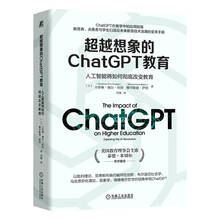公元前8000,非洲岩石艺术绘画
这幅岩画描绘了一只红白色相间的雨兽,它是给桑族人带来降雨的象征。桑族人相信,只有抓住并屠杀这种神秘的生物,雨水才会降临。这幅画现收藏于比勒陀利亚大学图书馆。数千年来,桑族人一直在非洲南部和东部,以狩猎和采摘为生,直到欧洲定居者到来。现在,他们仍然有一部分族人在纳米比亚的卡拉哈里沙漠地区生活着。
动物学习
求知是人的本性。
——亚里士多德
学习,自古有之,甚至在人类有历史记录之前。
尽管那时没有黑板课桌的学校,也没有拿着教鞭的老师。但是,人类滋生繁衍代代年年,学习与孕育相伴而生。人类的生存技术与生活经验,见闻习染,代代传续,是因为有学习。
假如到60万年前北京西南的周口店龙骨山走一走,你能看到一群最早能被称为“北京人”的类人猿:
砾石遍及的河滩上,他们打磨石块,学习怎样才能将石块制成刮削器、砍砸器与尖状器等劳动工具;
灌木丛生的山林间,他们奔跑追逐,围猎野兽,追捕跟踪,学习如何投掷石器,如何探查野兽足迹;
丘陵起伏的原野上,他们采集野生植物的果实或根茎,学习分辨哪些果实根茎能够食用,哪些有毒;
昏黑不明的山洞里,他们用火烧烤食物,围篝火长谈,分享经历,学习使用火,学习怎样保存火种。
很显然,这些远古时期的“北京人”已懂得学习,尽管这种学习与我们现在海淀黄庄的北京人学习很不相同。学习在现代,变为一种专门的活动。学习不再是一件随时随地自然而然进行的事情,也不再是混杂于吃穿行走之中的活动。
但是,当时的人类,和黑猩猩、大象、乌鸦无太大差别,黑猩猩也“学会”了做工具,大象也会“学习”分辨有毒果实,乌鸦还会往瓶子中扔石子喝水。
生物学家把动物划分成不同的“物种”,当时的人类被生物学家称作“裸猿”,和其他动物比起来好像也无太多殊异。
动物会学习?
人是唯一必须受教育的造物。
——康德(Immanuel Kant)
既然人类也不过是一种叫“裸猿”的动物,人类会读书会学习,那么,其他动物是否也会学习?
毛毛虫刚化蛹成蝶就会翩跹起舞,小鸭子出生没多久就能下水嬉戏,哺乳动物一出生就会找寻母亲的乳头并且会吃奶,蜘蛛从小会织网也是无师自通的。这些动物的行为似乎都是与生俱来,天赋遗传的,根本不需要学习。并且,除了人类之外,也没有一种动物学会识字读书,更不必说用“维基百科”网站学习。这样看来,动物应该是不会学习的。
但是,生物学家发现,一部分动物的本领并非天生遗传,而是在成长发育过程中,通过学习逐渐形成的新行为,尽管人们经常否认这一点,给动物“学习”加上引号。
20世纪60年代,动物学家辛德在大不列颠岛研究山雀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只山雀意外啄开订户门前的牛奶瓶,偷喝到牛奶。一段时间之后,大不列颠岛的每只山雀都“学会”这种做法,致使当地送奶工不得不在奶瓶上加扣一个杯子。而其他地区的山雀就没有大量出现过类似行为,表明它们没有学会这种本领。
不但动物会主动学习,并且人类还通过训练教动物学会一些行为。
19世纪末期,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进行了一系列著名实验。例如,巴甫洛夫在给狗吃肉之前总会按响蜂鸣器,因而,此后只需蜂鸣器响,就算没有肉,狗也会如同面前有肉一样流下口水。
条件反射的刺激多次训练后,动物便能表现出较为复杂的学习形式。例如,孩子想训练狗学习听令,他会拿一块肉骨头逗引狗,同时发出口令命其坐下后喂食。通过多次练习,哪怕孩子不给肉骨头,狗也会一听到孩子的口令就坐下来。
有人指出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实验整个都是人为控制的,在大自然中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动物并非真的会学习。
后来,又有了著名的“斯金纳箱”实验:把一只老鼠放到一方木箱中,箱中唯一可触动的物体是一枚按钮,老鼠按一下按钮,箱顶就会掉下一颗食物。如此这般,老鼠一旦知道了按钮事态反应,便会不断地去按,以获得更多的食物。“斯金纳箱”实验的动物能主动尝试把特定的动作同食物联系起来,但唯有当它们饥饿时,并且有食物犒赏时,它们才会做出这一系列的行为。
“斯金纳箱”实验的确是更接近自然的一类学习,大部分动物的觅食及躲避行为都是这种条件反射行为。许多动物像人类一样拥有好奇心,喜欢探索新鲜事物,就像小猫总是围着家中新出现的事物转,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以至于最后不出意外地打碎新买的花瓶。
并且,当一种现象反复出现,而没有产生有影响的后果时,动物对此的反应就又会逐渐减弱,最终视若未见。小鸡第一次发觉到头顶上掉下树叶时,它们显得特别警觉,会做出逃避或防卫的应激反应。但是,经历过几回落树叶后,其警觉行为便会弱化,对同一刺激的反应程度减轻。可是,若有新的物体从头顶掠过,如一只大鸦雀,它们会重新紧
劳伦兹和他的小鹅
张起来做出警觉反应。如此多次,小鸡学会了识别危险前兆的能力。
还有一类特定的动物学习行为,只在特定的时期发生。
动物学家劳伦兹做过一个实验:把鹅蛋分为两组孵化,一组由母鹅自然孵化并照顾;另一组用孵化箱孵化,并仅由研究员在场照顾。使人惊奇的是,后一组的小鹅把研究员当成妈妈。研究员走到哪,小鹅就跟到哪。假如把两组小鹅混在一起,当释放阻拦时,小鹅们立刻分成两路,一路朝向母鹅,一路则跑向研究员。
这种学习结果是由最初的印象形成的,被称为“印痕学习”。
“印痕学习”对一些新生动物很重要,它能够使那些刚出生、还没有生存能力的幼年动物,自觉跟随刚出生就照料保护它们的动物,让自身的生存和安全有所保障。据观察,许多动物都有“印痕学习”行为,如大多数鸟类、多种鱼类,还有绵羊、山羊、鹿等,甚至包括人类。
“印痕学习”是一类固定而有限制的学习行为,这些技能只在动物一生中某个特定时段能学会,其他时段都不行。例如,很多鸟类学飞都是羽翼将成之时,若在这个时段强制压抑幼鸟的习飞本能,从此它们就很难掌握高超的飞翔本领。像流传已久的“狼孩”学不会说话、缝住眼睑的新生猫看不到东西等传闻,正是因为动物在生命早期神经系统处于某种特定状态,而唯有在这段时期内,才能接受某一类刺激。从此,神经系统会变得不再能进行这种“印痕学习”。
除此之外,较高级的动物还有推理学习的能力。动物学家实验,把食物放在透明玻璃板后面,较低级的动物只会紧盯着食物兴奋地乱叫,或是乱爬瞎撞透明玻璃,而不知停息。可是,较高级的哺乳动物如黑猩猩能够很快就尝试绕过玻璃吃到食物。
著名的猩猩学习行为实验,也证实了黑猩猩确有推理学习的能力:香蕉挂在天花板上,屋内扔三只木箱,唯有把三只木箱垒起来,猩猩爬到箱顶,才能摸到香蕉。刚开始时,猩猩到处乱跑,之后它停下来,仿佛在寻找解决办法,最终把三个箱子搬到一起吃到了香蕉。
在大自然中,高等动物还学会使用工具。黑猩猩会用藤条来抽打其他的猩猩,还会用树枝伸到白蚁洞里掏白蚁吃。而我们从小就熟知“乌鸦喝水”的故事,并非传说,也是动物可以学会使用工具的证据。
植物也会学习
如果你想了解生命,就别去研究那些生机勃勃、动来动去的原生质了,从信息技术的角度想想吧。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不但动物会学,植物学家表示“植物的学习能力也很强”。
在名满天下的巴甫洛夫实验中,狗知道响声总会在吃肉前响起。植物学家在豌豆苗身上做了一个类似的实验:“肉”换成光照,“响声”变作风吹。
植物学家先测试了豌豆苗对风的反应,发现豌豆苗并没有什么反应。说明对豌豆苗来讲,风本身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提示,就好像巴甫洛夫实验中最初的响声。
植物学家放豌豆苗于Y形小室中,顺应植物向光性,挑一个枝条,用风扇吹,再在同一方向用光照此枝条。这个步骤持续几天,而且每天更换风和光照的方向。
因为植物的向光习性,豌豆苗本能反应是朝着前一天阳光照射的地方生长。但在第四天,研究人员打开风扇,并没有开灯。使人诧异的是,豌豆苗违背其本性,在黑暗中,大部分的豌豆苗都向吹风的方向生长。豌豆苗记住了这一关联——风通常在光的前面到来。
就传统而言,专家们会直接把学习现象与神经系统联系在一起。即使没有大脑的低级生物,也有神经系统,人们能够教会它们一些简单的刺激—反应行为。其学习方式也是通过神经系统的神经网络形成的,该网络能探测和处理外部刺激,调节行为反应。
但是,连神经元都没有的植物为何也拥有这种学习能力呢?
众所周知,记忆是学习的基础。
而关于植物,最神奇的一点,也是人类最难接受的一点就是,植物的记忆是分散的。植物的记忆并不存贮于某一个固定地方,比如树叶或树根。若是非要用传统的大脑记忆方式来看待植物的记忆,那么,只能把整株植物比作是一个大脑。
人类的记忆以电化学活动的方式在大脑中存贮、激活与传递。实际上,在植物中,同样有万千电学和化学信号在传播。植物和人类拥有一样的离子通道和相似的化学递质。
之前,人类总是一直以人的方式去理解,去研究其他事物,因而越和人类相近的东西,我们就研究得越深入。
假如是动物,在某种刺激下,我们能够观察到,动物身上的电化学水平波动。比如,我们能够在人身上插电极,观察他们在观看快乐或悲哀的图片时脑电波的变化。在动物身上,我们可以用相似的方式来研究。但是,对于植物,同样的方法完全无效。
于是,植物能够学习适应,而且还能在细胞层面保留记忆,这种观点显得新奇而有争议。但是,对植物行为的研究表明,这类看似很低级的生物完全可以在变化的环境内,和神经元一样有所感知,传递信息,并做出相应的决策,解决问题。
事实上,对植物行为的研究,可以回溯到19世纪晚期,著名的达尔文和他的儿子弗朗西斯就发现,植物的根茎上某些细微部分(被称为“根尖”),在执行类似动物大脑的功能。
很明显,植物学的研究发现,让我们意识到,只有动物会学习的想法是不对的,甚至学习也并非只发生在大脑这个器官中。
比如,秀丽隐杆线虫没有大脑,体内共有302个神经元。它看起来是无法进行哪怕最简单形式的学习,更别提发育的可塑性和社会行为了。
然而,如果一只线虫能在合适的温度下反复找到食物,它便会偏爱这种温度;反之,不再获得回报,它又会渐渐失去这种偏好。这样灵活的学习受到了NCS-I基因的影响。
线虫不仅可以学习,还会根据幼期的社会经验发展出不同的成年“个性”。研究人员敲击每个器皿的一边,让这些线虫逆转它们的移动方向。相比于独居的线虫,群居的线虫由于习惯了撞到彼此,对敲击更为敏感。
因而,不论是动物或是植物,假如它们符合人类一直以来对“学习”的定义,那么我们认为它们在“学习”。
基因在学习
在进化的过程中,互相竞争的主角虽然看起来是一个个独立的生物个体,但是真正的进化单位,其实应该是基因。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信息塑造DNA和生命结构,反过来又被其塑造。
——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
不仅植物会学习,以基因为介质的所有生物都会“学习”。
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提出以基因为生物进化核心的观念:“在进化的过程中,互相竞争的主角虽然看起来是一个个独立的生物个体,但是真正的进化单位,其实应该是基因。”
每一个生物体看起来好像是进化的主角,然而,小到单细胞的蓝藻,大到具有庞大身躯的蓝鲸、大象,不过是基因创造出来保护基因存活、促进基因传播、帮助基因繁衍的一种载体、工具或生存机器而已。它们存在的全部意义,完全在于基因存续。
因而,按照道金斯的逻辑,生物个体在学习,那么,作为生物种群的集合,基因也在学习。
基因是一种高效稳定存贮生命信息的完美介质,这无疑也是它成为“生命奥秘”的普遍承载者的根由。基因封装信息,并准许信息读取和转录。生命通过细胞扩散基因信息,生命体本身是一台信息处理器。生命体中的每一个细胞,都是纵横交错的通信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它们一息不停地发送和接收信息,不断地编码和解码。进化本身正是生命体与环境之间连绵不绝进行信息交换的外在体现,生命用基因来学习。
比如,将植物放在过热环境中,通过多代繁殖,它会适应,并在未来面临类似环境时更好地做出反应。这要归功于基因表达的改变。同样的事情也可以发生在单个植物体上,如前文的豌豆苗实验,充分刺激植物,其基因中的突变使之可以对刺激做出反应。
只不过,基因改变的这种硬编码的机械式反应,让人看起来像是植物本身在学习。并且,它们没有神经系统,也没有大脑,让我们人类从自身进行观察觉得有些奇怪而已。
不用说最简单的单细胞生命——细菌,更绝非一个典型的“学习者”。它们的一生,不但确定了“硬件”的构造,例如糖感应器和鞭毛,还写死了“软件”的内容。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被固化,没有学习改变的可能。它们永远学不会“应该游向糖多的地方”;相反,这个算法从一开始就被“写死”在它们的基因中。
但是,因为基因,作为一个物种的细菌,仍然存在某种学习的过程。细菌在物种进化过程中,通过多代试错,在自然随机的基因突变中,挑选出能提高糖摄入量的一些信息并传递下去。比如,一些基因突变帮忙改进了鞭毛等硬件的设计,还有一些基因突变改善了软件,类似执行“寻糖算法”的信息处理系统。
一切生命体都通过基因来存贮信息,基因也是一种编码、一份字母表。正如基因用6个G的信息表达一人,处于所有生命核心的是信息。
信息塑造基因和生命结构,并反过来被它塑造。那么,难道不能说基因和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完美的信息系统吗?
信息及其传输、保存和形成的结构,具有某种自然属性,至少在其初期是这样。50多年前,控制论先驱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就确定:生物同技术系统一样,都是在信息传播模式上运行的。
基因是一种极其稳定的信息存贮介质,同时,基因也存在一些机制,能改变基因的编码顺序,使生物的后代拥有一些新功能。当一个物种及其代表的基因即将灭绝时,产生新的突变对这一物种来讲特别重要,那些没有基因突变并适应新环境的大多数成员被淘汰,而少数幸存者的基因继承了一些新的信息,使其改变行为适应新的环境。也就是说,这一物种的部分成员历经一次次淘汰,一代代演变,在试错中不断学习前行。
学习并革新,生命的这种基本特性引发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原始基因库越来越拥挤,基因涌入新领域,诞生新物种。
最后,一系列特殊、全面的革新活动,在生命体内进行:感触环境,并将与环境有关的新信息储存在神经元上,而不再将这些信息进行编码并存贮到基因中。
生物体每时每刻都在自然环境中面临生死考验,其中环境信息至关重要。如果不能获取周围毒素污染的信息,秀丽隐杆线虫肯定夭亡。
于是,进化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特定功能的细胞,如神经元,连成神经网络,并最终形成大脑。
大脑反叛基因
处于所有生物核心的不是火,不是热气,也不是所谓的“生命火花”,而是信息、字词以及指令。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然而,如果基因是自私的,那么,大脑也可能会有自己的目的。
大脑通过四十亿年的进化,确实是有可能已超脱自私基因的掌控。在进化巨轮的推进下,神经系统的进化就演变为黩武穷兵的军备竞赛。
尽管意识到底如何产生,专家们还是言人人殊;人类有无自由意志,也还在争辩不休。但无法否认,如果承认人类有自我意识与自由意志,那么,自私的基因恐怕就不能在人类生活的世界中主宰一切了。
对自私的基因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自身的复制、物种的延续和生命的繁殖。然而,我们人类会违背传宗接代的自然目标,选择避孕、独身不生育,并非说我们做错了,也并非出了什么意外,而是我们的大脑会故意选择其他目标,反叛基因复制自身的目标。还有更难理解的极端例子,比如,为了信仰,选择终身禁欲,成为和尚或修女,甚至自杀。
为何我们会选择忽视甚至违逆基因及其复制自身的目标呢?
这是因为作为能够感知的生命体,我们只知道自己的感觉。尽管基因进化出大脑的目的是帮助其复制自身,但大脑其实根本上不在意这个目标,因为人类对基因完全没有感觉。
而且,实际上,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在大多数时间里根本不知道基因的存在。即使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基因的目标是复制自身,但是,我们鄙夷这个目标,视为老牛破车,不再重视它,甚至当作需要克服唯一障碍。
此外,我们的大脑认为自己比基因聪明多了,不会为某一个固定目标所驱使。
现代人知道他们喜欢甜食,是因为在食不果腹的原始时代只有尽量多摄取糖分的基因载体才能存活下来,但现代生活中日常糖摄入量已经过高,因而人们也开始欺骗基因,生产同样甜味但零热量的木糖醇代糖食品,这样仍然能获得吃甜食的满足感,而不用担心长胖。
人们已经意识到他们会产生性欲快感,是因为基因想要人类替它实现复制自身的目标,但他们并不想为一宵快活而终生受累,于是他们绕过基因编好的程序,采取避孕措施,而仍然能赢得基因对性行为的快感激励。
这意味着人类的行事方式,并不一定有利于生存竞争、繁衍子嗣或基因复制。实际上,因为人们更多地听从大脑的判断,而大脑判断的依据,并非只有几个简单明确的欲望目标。
因而,我们需要记住,现在掌权的并非我们基因,而是我们的大脑。
尽管这些欺骗或对抗基因机制的行为,并非总能奏效,例如上瘾,而且,我们的基因狡诈近妖,又顽固如石,人类基因仍然与几万年前黑猩猩的相差无几。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从此就不用遵守生物法则。我们仍旧是动物,我们的身体包括大脑,我们的理性与情感,仍旧是按基因“图纸”施工构建起来的。
通常来讲,假如没有发生基因突变,动物的行为就不会有显著的变化,包括最早的人类。两百万年前,依赖基因突变,才让会制作石器的“直立人”出现。而两百万年后,只要直立人未出现新的基因突变,他们制作的石器就不会变。
但是,“大脑反叛基因”之后,基因不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过去想要制造出新的石器、创造新的社会结构或是移居到新的地点,多半是因为环境压力带来的基因突变,而现在常常是因为大脑的选择。
正因如此,人类只花了几万年就变得与我们的祖先面目全非。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