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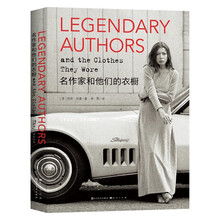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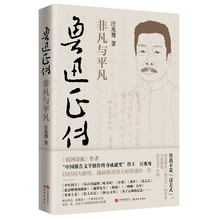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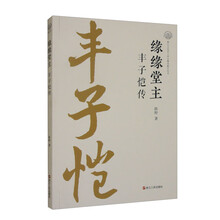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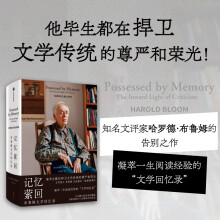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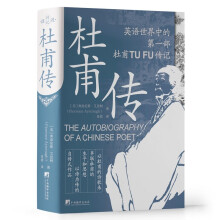
除了不朽的作品,这些作家的人生轨迹,也是一部部跌宕的传奇。
从高密乡野的放牛娃到诺贝尔领奖台的莫言;
漫天风雪独居山村写作的贾平凹;
满身风雨归国创业的江南。
在光阴的碎隙中,史铁生和他的轮椅碾过地坛公园的秋叶;
八月长安怀揣处女作,悄然穿行于未名湖畔的晨雾中;
陈年喜在矿洞深处,把诗歌刻进炸药箱的木纹……
他们是余华、刘慈欣、迟子建、金宇澄、苏童、王安忆、孙甘露、易中天、蒋勋、余秋雨、残雪、刘震云、许知远、当年明月、张嘉佳、杨红樱、郑渊洁、叶嘉莹、汪国真、金庸、唐家三少、南派三叔、江南、马伯庸、郭敬明、韩寒、刘同、大冰、笛安、双雪涛、李娟、安妮宝贝、亦舒、蒋胜男……
余华:人生就是出趟远门
余华出新书了,不过这次出的不是小说,而是一本散文集。2024年8月16日,余华新作《山谷微风》首发式在三亚阿那亚·三亚社区大草坪举行。该书首发式在抖音直播,超一百三十一万人在线观看,可谓是备受关注,连央视新闻也不止一次发文为其新书宣传。
其实,《山谷微风》同名散文最早发布于莫言的公众号,早在2024年4月就跟读者打了个照面。莫言还为好友余华认真地写了按语。
《山谷微风》收录了余华2024年全新创作的十二篇散文,及精选自1984年以来创作的十七篇散文,创作时间横跨四十年。在这本散文集中,我们仿佛看到另一个余华:松弛、自由,有平凡的烦恼和快乐,对生活充满细腻感悟与思考。
正如书中所说:“紧张还是放松,都是生活给予的,什么时候给予什么,是生活的意愿,我们没得选择,只有接受。”
从“冷酷杀手”“潦草小狗”及“小清新的温情大师”,余华的每一个阶段仿佛都在蜕变。似乎没人能想到那个写尽人间疾苦的名作家,有一日会有如此小清新的作品,甚至有些网友还担心它会像某些鸡汤文。
当读者粉丝们惊呼又被“知心小狗”治愈时,那个“酷哥”余华却好像已经在喧嚣中逐渐远行……
01 特殊的童年
余华,1960年4月3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
那是家家饥荒,青黄不接的时代。当时,余华的父亲华自治在浙江医科大学进修专科,正处于事业进取的关键期,很难为家庭提供收入。所幸母亲余佩文在浙江医院工作,保障了家庭的生活。不久,父亲毕业后也入职同一家医院。父母的职业让余华从小就过上一种相对优渥的生活。
余华和哥哥华旭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了人生之路。
兄弟俩性格相反,哥哥华旭天生性格活泼爱动,爱闯祸,余华听话而且胆小。
余华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他小时候与哥哥打架时总是被欺负,而他反抗哥哥暴力的方式是持续大哭,直到父母回来惩罚哥哥。这是一种面对暴力既胆小又渴望的态度,他不敢也没有能力直接反抗,只能期待更强大的暴力来制止暴力。
1962年,余华跟随父亲前往浙江嘉兴市海盐县,一家四口正式在此定居。因父母的工作原因,余华和哥哥只能被锁在家中。他俩只能隔着窗户认识外面的世界,看着田里耕作的农民,还有提着割草篮子在田埂上晃来晃去的孩子。
余华的童年几乎局限于家、医院以及附近的小村庄,而在医院生活的经历对其影响最深。
早期的余华跟现在“段子手”的形象完全不搭边。在所有新潮小说中,他是在主题和叙事上最“冷酷”的一个,这或许与他的特殊经历有关。
在余华读小学四年级时,全家搬进了医院的教职工宿舍,家对面就是医院的太平间。每隔几个晚上伴随余华入睡的是,各种悲惨和歇斯底里的哭声。
生死诀别时是最痛苦不堪的。面对这种惨景,余华在后来回忆中写道:
“我搬一把小凳坐在自己门口,看着他们一边哭一边互相安慰。有几次因为好奇我还走过去看看死人……”
最著名的事件当然是他跑到阴暗的太平间里睡午觉,因为那里的床非常凉快。他也经常看到父亲沾满血迹的手术服。那些鲜血、病人、生离死别对于幼时的余华来说逐渐变得稀松平常,可以说死亡原本带给他的好奇、恐惧,到最后只剩下了麻木。
余华讲这段经历时以开玩笑的口吻一揭而过,但对于那个胆小且敏感的小学生余华来说,真正的情绪是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毕竟那种经历,不管小孩还是大人都会觉得恐怖和害怕,并且无法接受。
或许正因余华这异于常人的童年生活,在他的作品中,死亡成为描写最多的主题。
02 疯子的世界
阅读余华早期的作品,你就进入了“疯子的世界”。在他的小说中有共同的主人公——疯子。最典型的就属发表于1987年第6期《收获》中的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小说中写了一个在特殊时期被折磨疯了的历史教师,人在1986年,精神却总是沉浸在1976年,沉浸在那个时期。最后,他用砍刀、烧红的铁块、钢锯等对自己施行各种酷刑,在令人恐怖的血腥场景中死去。
或许是因为真正经历过那段不堪的时光,相关的年少记忆实在太多。即便到了20世纪80年代,余华仍能看到周围残留的“影子”在做着“疯子”才干的事情。所以,小说中的历史教师才会那么娴熟地将刀狠狠对准自己。
1977年夏天,一项政策的恢复仿若一声惊雷,炸开了无数青年的心,现实为余华提供了一条明亮的道路——高考。
余华当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父母也帮助他全力备战。可那时的学生们并没有真正系统地学习过。彼时整个海盐县只录取了四十多名考生,应届生只有几名,余华名落孙山。
再接再厉的兄弟二人参加了第二次高考,却依旧以失败落空。就这样,哥哥去当兵了,而余华在父亲的帮忙下进入了武原镇卫生院。十八岁的余华,开启了他的五年牙医生涯。因为实在欣赏不了这个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余华为了进入文化馆而学习写作。
他最先接触的作品是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
这种散发着忧郁但唯美、温馨,饱含人情美和人性美的作品给余华带来了深深的震撼。此后,余华成为川端康成的迷弟,并一度影响余华后面的创作。
1983年底,借调文化馆工作后,余华陆续发表了一些小说,逐渐迎来了第一个创作高峰期。第二年的8月,余华正式调入海盐县文化馆。
当余华苦陷创作瓶颈期,而川端康成的作品再不能解决他的问题时,卡夫卡命运般出现了,还有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威廉·福克纳等现代主义作家。
那些颠覆性的艺术追求和对现实秩序的否定,使余华不再受限于普通的逻辑思维,而是彻底解放了创作主体的想象力。相遇是一种传奇,顿悟后的余华就此走上了先锋的道路。
1987年,余华发表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随后进入第二个创作高峰期,陆续发表多部中短篇作品。
在这期间,《死亡叙述》《往事与刑罚》《河边的错误》《往事如烟》等几部作品几乎都是直接描写死亡景象、事件或主题。当时的余华妥妥是一位“冷酷杀手”,每一部作品都得写死好几个人,并且画面极度血腥,令人头皮发麻。
这是一位“血腥暴力的杀手的狂欢”。
或许对于那时的读者来说,当余华出了新作品就会猜到他又要开“杀”了,更有甚者会猜这次死多少人,用的哪种死法。
因此,余华早期的作品总是给读者以十分残酷的“存在的震撼”与警醒,这也确立了其中国先锋作家的地位。
在他当时的作品中,情绪化的层面难以捕捉,但现实中的余华,却处处显露出悲悯的情怀。其实在那个创作时期,余华本人也不好受,甚至是遭罪的程度了。
“那个时候写了一堆的中短篇小说里杀了十多个还是三十多个……晚上尽做这种梦,不是我在杀人就是别人来杀我……我东躲西藏,醒来是一身冷汗,心想还好是梦。”
写小说能梦到被警察追捕和被人追杀,这也是独属余华的“幽默”了。谁能想到大作家余华会为了躲避警察而抱头鼠窜?此后,他再不敢写这种类型的小说了。
梦境在某种程度上是心理的一种投射,这正好印证了余华“冷酷”的背后有温情、爱和温暖。
03 人性的回归
1988年,余华进入了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创作研究生班学习。与他一起的还有莫言,两个人成了室友。
在那个时期,他们共同生活、学习,相互影响对方的文学创作。莫言已经因为《红高粱》而声名大噪,余华则是文坛的新星,正在冉冉升起。
他们在宿舍里一起写作,中间只隔着一个柜子,甚至能听到对方的呼吸声和笔尖在纸上的摩擦声。为了避免写作时互相干扰,莫言还在柜子中间挂了一个挂历。
当时,莫言在创作长篇小说《酒国》,而余华正在写《在细雨中呼喊》。这段学习经历让两个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路“相爱相杀”至今。
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是莫言的时代,一部《红高粱》让余占鳌的形象伴随着莫言的名字火遍大江南北。颇为戏剧性的是,就在余华奋力追赶老朋友的时候,莫言却由于《丰乳肥臀》的争议陷入了低潮期。
两个人的文学境遇,竟然如双生子一般,形成了对照。
1992年,《活着》出世,人性回归。余华在不断探索先锋道路时,终于意识到要脱离道德判断,用同情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
小说通过福贵的视角,讲述了他如何从一个挥霍无度的富家少爷变成一个贫穷的农民,他的家人和朋友一个接一个地离他而去,只留他一人与老牛在暮色中慢慢消失。
这些连续的死亡和苦难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展现了在苦难与不幸境遇中仍能活着的人性光辉。
活着的意义就是活着本身;活着就是最大的勇气和力量;活下去就是这一过程的全部意义和终极追求。
这部小说一经出版,随即大卖,之后更是经久不衰,多次再版,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活着”乃至“福贵”,都成了余华的代名词。
1995年发表的《许三观卖血记》继承了前面两部作品的内核。他用悲悯的幽默冲淡残酷的故事,给人物带来了生命,赋予了他们立体感和尊严。
从《在细雨中呼喊》到《许三观卖血记》,余华已然处于第三个创作高峰期。但读者的期待值越高,对作品的要求也会上升。
时隔十年,长篇小说《兄弟》终于在2005年发表。对于余华来说,他一直在寻找突破口,但这次好像并不理想。
俗话说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读者的反馈中逐渐出现了负面评价,相似的主题和写作手法仿佛只是前面作品的延续,这种“人道主义”方法已经用过了,人们早已失去了新鲜感。
余华在之后的采访中也表示,《兄弟》是他以为会好评如潮的作品,但没想到是批评如潮。他懵了,但也在继续进行艰难创作。2013年发表的《第七天》以及2021年发表的《文城》虽然成绩感人,但反响仍不及之前。余华自《兄弟》之后发表的作品总是质疑声、恶评不断,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否有人刻意贬低和抹黑的因素。
但是,余华的采访及作品产出的频率都在表明他的写作状态已大不如前。
“其实,我一直在抢救三部小说。有差不多三部小说,我写了一半以后搁浅了,现在正在想办法把它们救活,我也不知道哪一本书会先苏醒过来,都属于昏迷状态,你还得做人工呼吸,很累。”
在经历长期的失眠和焦虑后,随着写小说情绪的减淡和无力感的增强,余华又换了另一种方式活跃在大众面前。
04 形象的转变
2021年9月,“网红”余华上线。
其参演的电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上映后就属他的部分最出圈,“段子手”的形象初露苗头。
时隔多年,余华又回到了他的故乡海盐县。
“回首往事或者怀念故乡,其实只是在现实里不知所措以后的故作冷静。”
影片的最后,他在大海边行走,讲起儿时的心愿:“在我小时候,看着这个大海是黄颜色的,但是课本上说大海是蓝色的。我们小时候经常在这游泳,有一天我就想一直游,我想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天空中平静、广阔和灰暗的蓝与大海互相呼应,开放式的结尾让我们联想到作家们在自我探索和发展中的诚挚和坚韧。脱离这个范围,每一位为了生活而被迫成长的普通人亦是如此。
就这样,余华继续在网络上时而与莫言相爱相杀,被称为“潦草小狗”;又在众多的采访中化身“段子手”,得到年轻人的追捧。同时,他由于真诚“接地气”,成为年轻人的“知心小狗”。
世界破破烂烂,“潦草小狗”缝缝补补。那个“杀手”余华已去,治愈大师正式上线。
从1983年开始,余华在写作的道路中行走了三十多年,踽踽独行。余华的这次转型,是对故乡的回望,也是对自我归属的探索。
近几年,余华的作品多为散文和随笔。时代发展飞速,现在的余华在现实平淡的生活里继续写作,从山谷里的微风徐徐,联想到少年时在炎热夏天寻找的穿堂风和蒲扇风。
“小时候的人生是向前看,现在的人生感受是往后看,回忆占多。”
人不可能永远在那么一个好状态里,作家有时候也需要一点运气。余华在近期的采访中表明当年的感觉正在远去,即便现在的身体仍然维持着激烈的状态去创作,但感觉没了。
这种感觉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最好状态时的时间被“玩”掉了,剩下能好好创作的,也就只有十年左右。要找回好状态来,很困难。
虽然有网友调侃,六十岁正是奋斗的好年纪。但人到六十,目标曾是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靠近,有野心的余华也终于发现自己和他们的距离不可逾越。
在新书《山谷微风》的发布会上,电影《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留白得到了新的填补:“这是我的亲身经历。之前我一直以为游向大海深处看到的是蓝色海水,有一次在杭州湾游泳时,游到离海岸线很远的地方,发现海水是绿色的。
“后来是海流把我推回了海岸,可以说是一次劫后余生的人生经历。”
1986年,二十六岁的余华带着未发表的作品《十八岁出门远行》参加《北京文学》笔会。在会上,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李陀审读完肯定:“你已经走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列。”
此后的余华越写越胆大,这几十年真正走在了先锋的最前列。
时光轮回,曾经的先锋如今仍然笔耕不辍,却是为了更好地找回自己。余华选择留在三亚继续写作,希望把感觉找回来,争取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里补救搁浅的小说。
维吉尔说:“一丝微风勉强把他们的名字吹入我们耳中。”在历史的长河里能被微风吹进耳朵的人是极少数的。
在这个喧嚣的信息社会里,余华仍旧保持着缅怀、沉思与关怀。只不过,作为当代作家中一个特殊的存在,注定了要继续独自前行,以遗忘的姿态留在这长河中……
作家精彩名句与段落摘录
名句
1. 我不再装模作样地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在细雨中呼喊》)
2. 我的悲伤还来不及出发,就已经到站下车。(《第七天》)
3. 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活着》)
4. 做人不能忘记四条,话不要说错,床不要睡错,门槛不要踏错,口袋不要摸错。(《活着》)
5. 这就是人世间,有一个人走向死亡,可是无限眷恋晚霞映照下的生活;另两个人寻欢作乐,可是不知道落日的余晖有多么美丽。(《兄弟》)
段落
1. 他们脸上的皱纹里积满了阳光和泥土,他们向我微笑时,我看到空洞的嘴里牙齿所剩无几。他们时常流出混浊的眼泪,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时常悲伤,他们在高兴时甚至是在什么事都没有的平静时刻,也会泪流而出,然后举起和乡间泥路一样粗糙的手指,擦去眼泪,如同掸去身上的稻草。(《活着》)
2. 我的生命在白昼和黑夜展开了两个部分。白天我对自己无情的折磨显得那么正直勇敢,可黑夜一旦来到我的意志就不堪一击了。我投入欲望怀抱的迅速连我自己都大吃一惊。那些日子里我的心灵饱尝动荡,我时常明显地感到自己被撕成了两半,我的两个部分如同一对敌人一样怒目相视。(《在细雨中呼喊》)
3. 文学的叙述就像是人的骨髓一样,需要不断造出新鲜的血液,才能让生命不断前行,假如文学的各类叙述品质已经完成了固定了,那么文学的白血病时代也就来临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主编说...........I
数星星....................................I
一个问题与三个答案......................V
第一章 土地、创意,他们曾成为先锋 001
莫言:不只是诺贝尔文学奖...................................002
余华:人生就是出趟远门...................................009
史铁生:命若琴弦...........................................018
刘慈欣:《三体》爆火后........................................027
贾平凹:一脚踹破这潼关.....................................034
迟子建:谁能代表东北文学..........................040
金宇澄:《繁花》背后............................049
苏童:大红灯笼高高挂.....................................057
王安忆:我不是一个原地踏步的人.......................066
孙甘露:重回文坛之巅..................................075
第二章 认知、思考,他们曾发出声音 083
易中天:道路曲折我走不完.............................084
蒋勋:蜗居陋室.......................................092
余秋雨:人生转过几次身.......................................098
残雪:人生何必诺奖.....................................105
第三章 世界、是非,他们曾云淡风轻 111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112
许知远:挨骂最多的文艺青年....................121
当年明月:成名始末...........................................130
张嘉佳:走,吃饭喝酒去........................140
杨红樱:塑造一代人的童年...................149
郑渊洁:退出作协...........................................156
第四章 诗歌、腔调,他们曾吟诵人生 163
叶嘉莹:悠悠百年,赤子诗心.....................164
陈年喜:炸开那座山.........................................172
汪国真:人民说你是诗人.........................................183
第五章 虚构、想象,他们曾缔造传奇 191
金庸:谁都有一片江湖......................192
唐家三少:网文之王.........................201
南派三叔:他还是回来了...................................208
江南:逐渐“老贼”.........................................214
马伯庸:小人物最擅长刻画小人物..............................221
第六章 年少、敢为,他们曾开辟阵地 231
郭敬明:谁能缔造青春文学..............................232
韩寒:我所理解的生活.............................241
刘同:不是“文艺青年”............................249
大冰:江湖再见.............................................257
笛安:打破标签........................................267
双雪涛:砸掉铁饭碗之后.......................275
李娟:天生的作家.............283
安妮宝贝:一个旅人走到新的边界..............................291
第七章 风花、雪月,他们曾书写爱情 299
亦舒:我在感情上浪费太多时间了................................300
八月长安:青春是座巨大的乌托邦.........................307
蒋胜男:出圈背后,藏着六亿女性的痛 316
温馨提示:请使用泸西县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淄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葛思绪:
“‘投稿指南’公众号总能在更新中给人一种惊喜,很多依然闪耀在中国文坛上的作者,能以一种别开生面的方式被他们娓娓道来,让我们在了解作品的同时能够获知作家本身的经历。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有时未必高于生活,我们常常忽略,每个作家背后的故事,也许是比文学作品本身更动人的内容,这也是‘作家野史’栏目能够在互联网上引起广泛阅读的原因吧。”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北京市长城学者,中央广播电台节目评审专家杭孝平教授:
“在注意力即生产力的今天,各类媒体炮制的信息泡沫,在满足受众网络生活各类需求的同时,也消解了观众对深度阅读的耐心和关注。‘文学’作为一门相对严肃、古老的艺术显学,好像与生俱来就带着一种与娱乐、商业天然相悖的清冷气质,这似乎注定了其在互联网趋利、追逐热闹风气里被处处掣肘的命运。在新的传播渠道和内容呈现上,如何发掘、释放其传播潜能和文学价值,是当代文学人理应面对的问题,也是像‘投稿指南’这样的文学类自媒体为何存在、持续探索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