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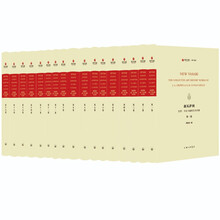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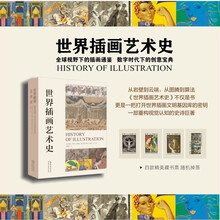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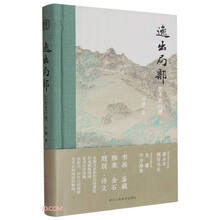



《喧嚣与孤寂 : 二十世纪美术史研究札记》是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王犁的一部美术史研究论文集,收入作者近十年来有关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研究的论文十篇,另有一篇美术史研究者刘新撰写的前言和作者的一篇“代跋”。在二十世纪美术史研究的整体性之外,作者选取了更为个人化的视角,对一些主题和艺术家做了大量的文献梳理,努力呈现一种历史事实,进一步探究艺术与时代的关系。同时,作者有从事美术实践的经验,撰写研究文章多了些感性体验与趣味,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史论。
代跋:谈美术史研究
范景中先生有一篇讲稿《美术史在人文学科中的地位》,从张彦远、米芾、董其昌到瓦萨里、温克尔曼、黑格尔,中外古今娓娓道来,讲述美术史研究对于了解一个时代的意义。在范先生看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学术真正达到高水平的话,那么它的美术史一定有很高的水平。如果它的美术史不高的话,它这整个学术水平不会是很高的。我讲这些也是在暗示美术史在人文学科中的地位。它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在瓦尔堡看来文艺复兴是西方文化发展的奥林匹克站,代表着西方文化发展的顶峰。既然有顶峰,价值观就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是真正伟大的艺术)这是价值体系的表现。这是二战之前西方人文学者所坚持的观念:研究艺术史是带有价值观的,跟考古学不一样,考古学上只要你是古代的我就要挖掘,不管价值只管对象,是value free。但是美术史不一样,是带有价值观的”。也就是说,这里涉及美术史研究 对象和美术史研究学科本身,美术史研究应该成为可以给人文学科带来光荣的学科。
近百年来中国美术和美术教育的学院化进程中,各种思潮进入,中国的知识界面对西方思潮的反应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但是,不难发现大体上有一个规律,这就是学术最活跃的时候,往往也是学术思潮争鸣最乱的时候,“乱”好像是个贬义词,按现在流行的说法其实就是多元的局面。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知识界,既有应对西方文化思潮冲击后的学科梳理,又有在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对传统文化时的现代转型。这种应对的局促在亚洲并不是孤例,记得几年前读《日本绘画史》(秋山光和著,常任侠、袁音译,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版)的印象,日本这个民族对外来文化的接受,不管是开始的“遣唐”还是“遣宋”,或者明治维新后的“遣欧”,都不乏对外来先进文化保持奋不顾身的虔诚,而在美术史的线性发展中总保持着边学习边消化的习惯,时刻有维护民族文化身份的警惕。这里也涉及美术史叙述的对象与美术史叙述的方法。
范景中先生在那篇讲稿中提出现代美术史研究的处境与担忧:“因为我们现在美术史虽然在中国已经兴起了,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西方的视觉文化对中国的美术史研究的冲击。视觉文化就是value free的,就是从人类学或者其他任何角度考虑,但就是不从价值的角度、不从风格的角度、不从艺术的高低的角度来研究。于是,很多西方的美术史家实际上是看不懂画的。布克哈特把人文科学归为Bildung(教化),而不是Wissenschaft(科学),所以他写作和讲课的目标是Genuss(乐趣),此词虽涵有通过艺术而获得秩序与和谐的体验的愉悦感,但更重要的是把最高的人性和道德的价值 归因于这种体验。”这也正是美术史学科本体特性值得讨论的一个话题。
从我自己的体验来说,今年实践类博士研究生刚毕业,常有朋友问我读博的最大收获是什么。我说是文献阅读能力提高了。记得当初开题后向任道斌老师请教博士论文的写作,任老师强调实践类还是要发挥自己实践的优势,要把自己实践的经验带到研究中去,实践经验肯定包括审美经验、技术体验、形式语言等具体的感受。我的博士论文最初的主题是“傅雷视野中的中西美术交汇”,开题时老师建议缩小到“傅雷与黄宾虹”,在博士论文撰写过程中进一步缩小到“有关傅雷与黄宾虹几个常见问题的疏证”,最终完成稿十多万字就是解决三个问题:第一,黄宾虹生前究竟有不有名?第二,黄宾虹认识傅雷前后的国际视野有没有变化?第三,傅雷到底为黄宾虹做了什么?整个论文的撰写,虽然最后又回到了文献材料的梳理,但任道斌老师的话一直贯穿我论文写作的始终。
傅雷并非一个美术史家,应该是一位优秀的美术批评家,他并没有美术实践的经历,但在那个时代却比很多人都要理解黄宾虹先生的艺术。通过留存的书信我们也知道傅雷理解黄宾虹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给黄宾虹操办“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时写下的《观画答客问》,几乎是那个时代理解黄宾虹艺术最好的文本之一。在王中秀、洪再新、李伟铭这一代学者前,研究黄宾虹艺术的文章里最好的应该是傅雷的《观画答客问》、瞿宣颖的《宾虹论画》、张宗祥的《谈谈黄宾虹的画》、潘天寿的《黄宾虹先生简介》等寥寥几篇,当然还包括施翀鹏(南池)的《略有瑕疵的黄宾虹》——这篇文章因为发表在1947年《艺术论坛》创刊号上,相信黄宾虹先生本人也能读到。这些文章基本代表那个时代专业人士对黄宾虹的看法。我们不要简单地把那个时代的学人笼统地褒扬为学贯中西或古今兼善。从傅雷出身和出国前的就学经历看,他已经有新学的背景,后来他给刘抗的信里也谈到自己对传统文化和传统书画的兴趣是伴随年纪增大而增强的。傅雷在与黄宾虹通信中请教其用印“竹北簃”的释文看,说明傅雷没有旧式文人具备的说文基础,但并不影响他对那个时代艺术的判断能力。瞿宣颖是那个时代的著名诗人,因抗日战争期间附逆成为落水文人,而淡出大众的视野。张宗祥身为学者、书法家,兼善丹青,潘天寿、施翀鹏以画名世,现在看潘天寿是大画家,施南池仿佛不太有人知道,但在那个年代的上海,大家对潘天寿和施南池的了解,差距不会像现在这么大。我们可以从他们论述黄宾虹的文章里读出,身份背景不同对相同个案的表述间的异同,或讨论问题的表述方式,或自己实践经验的直接或间接的带入。其实傅雷《观画答客问》里对中国画欣赏的几个境界,几乎与黄宾虹给顾飞的信里讨论看画经验相同,《观画答客问》里经典的表述究竟来自傅雷还是来自黄宾虹?相信傅雷深深地被黄宾虹的艺术和对艺术史的见解吸引。
在研究中国美术史时,我们不可能无视中国美术史自身的变化,张彦远、董其昌、黄宾虹对美术史话语的贡献,还有谢赫的“六法”论。张彦远、谢赫并不是历史上留名的大画家,董其昌、黄宾虹在美术史上已有崇高的地位。而黄宾虹先生对美术史认识的三个阶段——从与大家一样崇古言必唐宋,到对明中期艺术家的认可,再到从金石入画的美学思想的梳理中产生对“道咸中兴”画家的再认识,特别是晚年对乡邦文化中一些小名头画家的热情,虽说是美术史观的变化,却也离不开黄宾虹绘画实践认识深入带来的影响。
中国画本体是笔墨,笔墨既是技法又是审美,涉及对笔性、线质的理解,黄宾虹将其概括为平、留、圆、重、变。记得朱豹卿先生上大学时,班上同学怂恿作为班长的他去请潘天寿先生讲讲笔墨,潘先生回答:“笔墨一步一重天,不可言说,还是讲讲构图吧!”朱豹卿先生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也不要把“笔墨”神秘化,应该有可讲的部分。假如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者有一定的笔墨经验,当然有助于其对古代绘画作品的欣赏,但没有笔墨的实践经验并不全然等于没有在欣赏中积累的审美经验。傅雷先生这样具有高水平的审美眼光的人,虽在不能译书时有学习种花和临帖学书法的记录,但一辈子并没有自己动手染翰的经历。近代美术史家中理论实践兼善的如陈师曾、潘天寿、郑午昌、傅抱石、俞剑华、童书业等,大概都受日本美术史家通史撰写的影响,撰写美术史的本意大多为教学需要,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中有关明清的章节有一些明显带有实践者体悟的言辞,应该是潘天寿先生这本著作出彩的地方。
我在博士论文的撰写过程中,在涉及黄宾虹国际视野的研究时,明显觉得自己对近代思想史不熟悉,包括中国士人的天下观、大同思想与后来的国际视野,特别是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变化,还有黄宾虹的好友邓实的民族主义思想,假如有这些知识储备,我会进一步深入理解黄宾虹涉及欧美话题的言辞。美术史研究跨学科的趋势肯定是好事,近代美术史研究一路走来,回望那个年代美术史家的优势和局限,会有更多的借鉴,多元肯定比一元好。近些年西方汉学中美术史研究的成绩,也促进了中国美术史研究现状的改变。另外,有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背景的学者参与,只会为美术史研究带来更为丰富的资源。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关系和其他学科的资源之间并不是A和B的关系,实际上中间还有一个大写的“人”字,作为主体的消化能力和驾驭能力才是关键。
记得有位当代美术史家提起当今学者的水平时,谈到“当今一流,放到民国二流,放到晚清是三流”时其言也慨。但在他为自己叫好的画和字里却看不到他在文章里的才气,反而不如上一代文人如张宗祥、夏承焘那一辈学人偶涉笔墨,虽然有时画面不完整,但气息雅致,艺以人传。
情怀与发现 刘新
谈浙派人物画研究
浙派人物画缘起与影响
潘天寿的人物画
从诸乐三的速写谈起
黄羲的早期活动信息
激越年代的努力
——1949—1976年浙江美术学院素描教学变迁
丁立人的美术史意义
黄宾虹《临倪瓒山水图轴》
应均现象谈
1960—1966年的林风眠与傅雷
——《傅雷家书全编》钩沉
代跋:谈美术史研究
温馨提示:请使用泸西县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