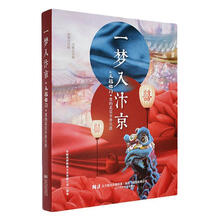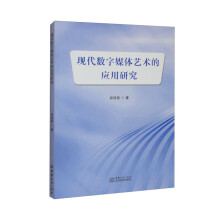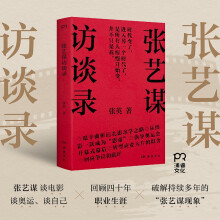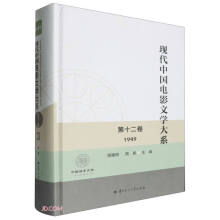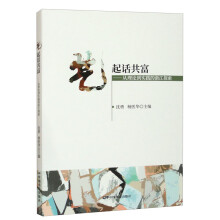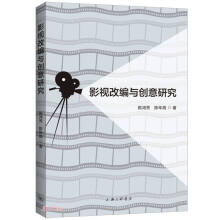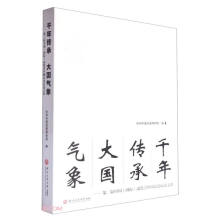《克里斯托弗·诺兰电影文化研究》:
二 道德逻辑的模糊
在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谱系中,道德从来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无论是植根于哪种文化之中,道德都会衍生出一系列较为类似的认知概念,如正直友好、真诚善良、团结互助等。这些相似的认知概念不仅为产生于各种文化之中的法律提供了可借鉴的模板,也为法律的制定奠定了具有共同心理特征的基础,还为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构建了可行通道。因此,对于道德的阐述始终都是社会学与哲学的研究重点。自中世纪以来,特别是在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等各方面因素的促使之下,西方社会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而在导致这些变化的诸多因素之中,康德(ImmanuelKant)的道德哲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康德看来,道德哲学可划分为三个层面,分别是“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从大众道德哲学过渡到道德形而上学”和“从道德形而上学过渡到实践理性批判”。而在邓晓芒教授看来,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实际上呈现出了明显的由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层次,即由通俗道德哲学向道德形而上学、继而向实践理性批判的演进。在通俗道德哲学层面上,康德由普通大众的日常道德观念切入,指出人的理性是一种“应当给意志以影响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最重要的意图是实现包含着善良意志在内的“义务”,只有出于这种义务的行为才是具有哲学性质的道德理性知识。作为一个普通人,“即使不教给他们任何新东西,只需像苏格拉底所做的那样,使他们注意自己固有的原则,因而不需要任何科学和哲学,人们就知道如何做才是诚实的和善良的,乃至于智慧的和有德的”。当然,这种通俗道德哲学仍然保留着素朴的本质,它仍然要依据更高级的哲学指导下才能发挥正确的作用,因此其必然要上升到道德形而上学。在道德形而上学层面上,康德实际上是将其淬炼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即将人的行为准则上升为自然法则,只有这样才能在任何条件和前提下均能成立,并展开对于“道德律”的自然淘汰。不仅如此,康德还认为,主观目的是可以随时变化的,只有客观目的才是一切理性者普遍且必然的目的,这种客观目的就是“人格”。也就是说,康德认为真正的道德要以人为目的,而不是将人当作手段来使用。在尊重人格的基础上,康德提升了自由意志的权威,认为每个人的意志都是立法的意志,只有自律才是最高的道德律。正如其所言,“有理性的存在者任何时候都必须把自己看作在一个通过意志自由而可能的目的王国中的立法者”。而在实践理性批判层面上,康德主要考察的是道德律如何成为现实并发挥普遍作用的问题。他认为,如果要使意志的准则成为普遍法则,那就必须通过“自由意志”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因为在他看来,自由虽然是先验的,其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但是“因为如果不是道德律在我们的理性中早就被清楚地想到了,则我们是决不会认为自己有理由去假定有像自由这样一种东西的(尽管它也并不自相矛盾)。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