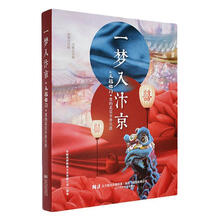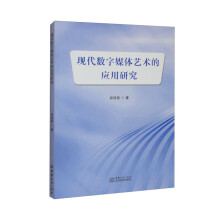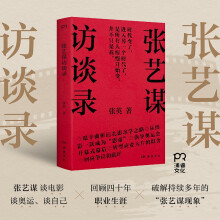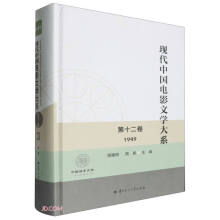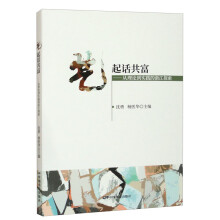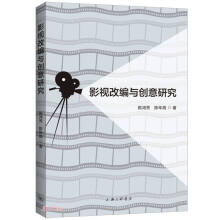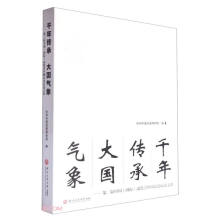《视听的言说:关于影视艺术的存在性研究》:
第一,可以获得知识。这个知识包括了陕北的风土人情、特定历史下的政治生态,以及农业生产上的一些知识。一个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阅读完小说以后,或许可以感受到比教科书上更为真切的“历史”,因为我们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形象地获得这些知识的。
第二,可以感受到对象性情感。对象性情感是指具体的情感,它未能脱离作品。比如读者被书中的情节吸引,被其中的人物遭遇感动,这些都是与作品内容相关联的,所以是具体的,也是对象化的情感。假如有读者和书中人物有类似的遭遇,他会感同身受,甚至会与主人公一起悲伤、一起流泪,这虽然也是一种情感体验,但这种体验还只是局限在作品和读者自身,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说法,我们读出的只是作品中“自道身世之戚”①的情感,这种情感未超越具体的情感,它属于对象性情感。
第三,可以体验到生存情感。生存情感超越了具体的情感,它是与人对“超越性存在”的领会相关联的。此时的作品为读者打开的是一个生存的语境,这个语境是我们对生命感受的体验,它是我们“对象性”语境和情感之根由。所谓根由,也就意味着这种语境是那些“具体的”或“对象性”语境和情感存在的前提。《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身上发生的故事,构成了对象性语境;他的欢乐和痛苦构成了对象性情感;他的体验构成了对象性体验。如果一部“作品”只是由这一系列“对象性”元素构成的话,那么它记录的只是“事实”,尚未构成艺术作品。路遥写孙少平的遭遇,不只是想让读者了解这一人物的遭遇和不幸。路遥为我们打开的是一个生存语境,他通过孙少平的遭遇和不幸这一对象性事件,让读者领会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在命运面前人之选择的无奈和悲怆,这就是人的生存语境。因此,作家的匠心无非是为读者建构此种语境提供可能,唯有进入此种语境,作品才是作为“作品”而存在,它才是“真理的原始发生”。当然,这种语境不是文字直接给予读者的,而是读者通过领会自行创造的。当读者通过作品领会到了生存语境,此时艺术作品便自行显现了,由此才有了美的发生。
综上所述,只有人在以上第三种情况下,也就是体验到生存情感时,作品的物性才能真正被开启,艺术作品才能真正地得以显现。作品的“存在”原本就在物中,它是“物之为物”的显现,即“物之灵化”。作品都有其物性,比如语言是文学的“物”,声音是音乐的“物”,石头是雕塑的“物”。“灵化”了的物就不是作为“质料”的物,而是作为“特定的感性的物”。所以,在以上的第一、二种情况中,语言只是知识和对象性情感的工具,它是作为“质料”的物而存在的。而只有在第三种情况下,语言才显示出人对“超越性存在”的领会,即显现其自身,语言的物性才真正被开启,成为了“灵化”之物,艺术作品也由此得以显现。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