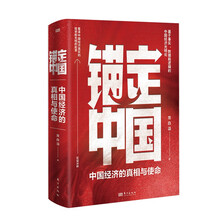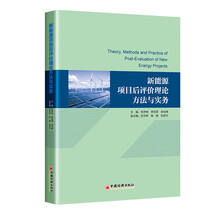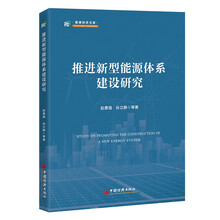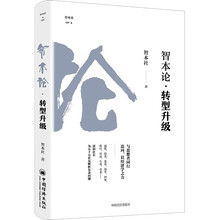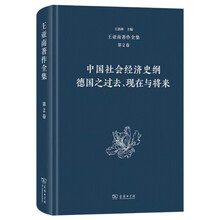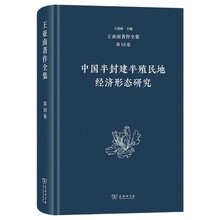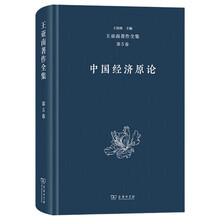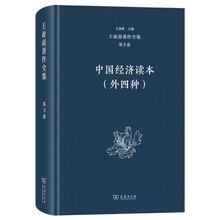《中国经济复杂?:通宏洞微视角的洞见》:
(四)前景展望
有趣的是,复杂性研究在微观理论中的前沿性变革并未引起宏观经济学的相应变化。事实上,美国宏观经济思想的演化走的是另一条路,也就是说,20世纪60年代,宏观经济学中的简陋模型正在转变为基于抽象的代表性主体模型及其均衡假定的理论性分析框架。这些宏观研究打着新古典、真实商业周期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的名义,并已在美国成为主流。
宏观理论的这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正如新研究所表明的,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宏观理论声称拥有更强的理论基础,而它得出的很多结论并不被经验证据或理论所支持。但是,当新理论模型成功排斥了旧理论时,人们并不清楚新理论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宏观经济有什么增益。在最好的情况下,新宏观模型的结果可以与经验证据大致校准,但这些新模型的校准常常并不比其他模型更好,而它们更受偏好的唯一理由是审美意义上的——它们具有微观基础。但是,这是一种奇怪的微观基础——它基于不存在异质性主体相互作用的假定,而就很多人的直觉而言,正是异质性主体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宏观经济的重要特征,这正是“凯恩斯悖论”的深层原因。
从复杂性科学角度看,宏观理论前沿研究的发展并不在于围绕代表性主体的微观基础,而在于超越传统理性和均衡框架。也就是说,宏观经济被视为内生组织而成的。问题不在于宏观经济中为什么会有波动,而在于为什么微小的不稳定能够通过复杂的相互作用导致混乱。很难相信人们可以发展出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而无须考虑宏观系统对个体的反馈作用。尽管推动宏观分析理论以发现其是否能在短期内提供见识依然有其意义,扩展这种基于远离现实假定的分析可解的纯理论模型对于政策指导并无帮助。当没有纯理论基础时,宏观政策最好基于统计模型、大数据,探讨深化微观分析,促进宏观建模分析的实质性进展,进而为计算社会科学等相关多学科的大跨度、深度交叉融合发展探索新途径。
毋庸回避,处于萌芽状态的复杂经济问题研究或复杂性经济学也面临着一些障碍。这些障碍主要包括:经济学传统观念的强大力量和惯性;现实复杂性程度衬托下的现有工具方法的局限性;基础理论层面的对接,寻找的切人点和结合点尚不突出,关键性和要害问题的提炼表述不确切;自然系统复杂性的方法平行类比研究社会经济复杂性时暴露出的偏狭和固执,未显现出在解决重大复杂现实问题上独特的功效和威力;已有的零散的理论和应用成果缺乏凝聚和串联,未形成整体优势和清晰预见的发展力量;等等。
复杂性经济理论将经济系统视为一个动态系统,均衡经济学强调秩序、确定性、演绎和停滞,复杂性经济学则着重偶然性、不确定性、心理作用和对变革持开放的观点。在复杂性经济理论结构框架创建过程中,数学方法不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唯一演绎推理途径,均衡经济被看作非均衡经济和复杂性经济的一个特例,复杂性经济可以以更一般的方式来处理经济问题。复杂性经济理论为经济结构自我提升、理论创新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对复杂经济问题的研究.正在孕育和形成强劲有力的分支学科,复杂性经济学蓄势待发,虽然不能由此奢望一定能从源头遏止和彻底解决危机问题与异常现象,但人类预见、控制和应对这类复杂局面的能力必将得到实质性提升。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