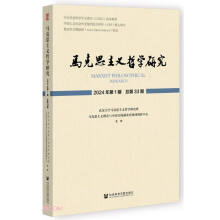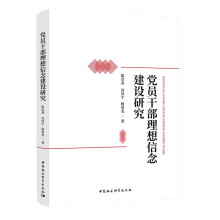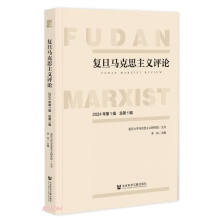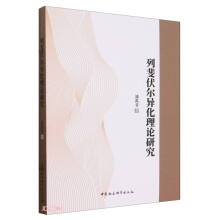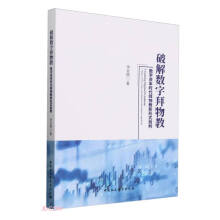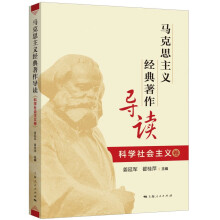导 语
这是一部内在性评论 (intimate commentary)的著作。在我想到那些安然塌边和美妙地依偎在沙发上的诱人的马恩卷集之前,让我来说明一下,我说的“内在性”是针对文本,特别是对那些一手材料所进行的耐心细致的阅读。这就要求读者对文本不能操之过急,注意文本中不同的转折 (twists)、矛盾、问题和洞见。我必须承认,这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数量惊人。我可以说我对他们的作品已经谙熟于心了。事实上,这种方法的源头正是古老的 《圣经》评注。它通常被那些与世隔绝的 《圣经》评注者所使用,如今它可以应用在各种文本中。
我需要说得再具体些:这是一种神学评注。这样讲的意思并非诉诸某种超验的权威来评估马克思与恩格斯,绝非如此。相反,我读他们作品的时候,非常注意倾听常常出现的不同的神学典故、引用、暗流、反抗和论点。在这一过程中,当我感觉到他们有所不足时,就会与其商榷。研究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宗教”问题并不是一件新鲜事。① 但我还想说得更具体些,他们竭力研究的并不是 “宗教”,而是 “神学”,通常就是 《圣经》问题。② 有一种观点我无须说明,但在此仍要提及一下,即在浸满了基督教遗产的欧洲,“宗教”确实意味着基督教神学。即使在今天,“宗教”仍被用来当作神学的替代品。每当我听到这个术语的时候,我都觉得我需要进一步说明我们所谈论的宗教是建立在什么意义上的———是历史的、社会的还是文化的。这也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与恩格斯。
我对马克思主义者处理神学的方式不再感到意外,显然,神学是研究子虚乌有之物且没有独立发展史的一门学科。当我开始这一计划 (这是第四卷)的时候,我接触到的材料数量超出了我最初的想象。那些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地创作出大量的神学研究作品。阿多诺、布洛赫、本雅明、卢森堡、考茨基、戈德曼、阿尔都塞、葛兰西、列斐伏尔、汤姆森、齐泽克、巴丢、伊格尔顿……还有许多未列出的学者。因此,现在到了转向熟悉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艰巨任务的时候了。
站在他们与神学互动的大量文献前面,我不止一次希望能抽一根烟,来帮我思考到底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我本可以选择复述业已成为标准的东西,让我的整篇讨论在人云亦云的 “思想发展”模式下展开,即它向黑格尔、费尔巴哈或共产主义的各种 “转化”。① 遵循这条路径,我本可以选择这一轨道中最终通向 “成熟”时期历史唯物主义的线索。但问题是,一个人的思想从来不会严格按照时间的顺序发展,也不会按照作品发表 (或未发表)的顺序出现。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晚年对神学的持续兴趣 (这样就)说不通了———比如,马克思对拜物教十分着迷;恩格斯一直在关注基督教及其起源。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