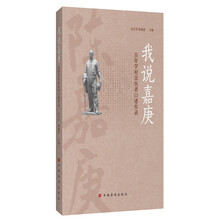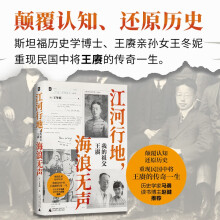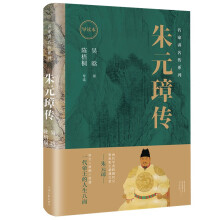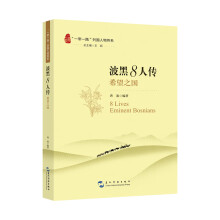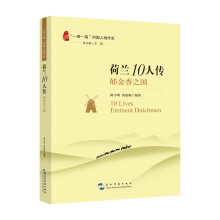《陈独秀正传》:
002.从被动读经的少年到接受新学的康梁派
这次难堪的乡试是陈独秀人生之旅的一次大转折。
乡试期间,他结识了安徽绩溪的秀才汪希颜,汪希颜以著名廪生胡子承(晋接)为师,推崇维新,研习新学,此时他刚进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陆师学习。陈独秀从此初尝维新思想的甘甜,茅塞顿开。他对自己进行反思,从6岁开始读书,至17岁考中秀才,被旧文化教育环境所局限,如井底之蛙,鼠目寸光,无法接触新事物,思维僵化,对国家政治状况毫不知情。
回到安徽,在汪希颜的引荐下,陈独秀密切接触了汪希颜的胞弟汪孟邹、李光炯、邓艺荪、江讳等皖省维新派人士。《时务报》当时是宣扬维新思想的载体,在他们中间流传,让他耳目一新、热情昂扬,他成了识“时务”的俊杰。此时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处于同封建顽固派激烈论战中,正面交锋如火如荼、声势浩大。这是变法的前夜。陈独秀感觉酣畅淋漓,大长见识。顽固派坚守“祖宗之法”,决意“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坚持科举制度,反对西学;维新派坚持进化论力挺“变”,以“变”兴国,抨击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着的愚民政策,“牢笼天下”“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揭露八股取士制度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等三大罪状,指明“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提倡普及文化教育、设立新式学堂,造就维新人才,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
陈独秀和这几个维新人士密切交往,着重讨论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他在康梁学说的耳濡目染下接触了西方文明和现代科学知识。维新领袖的政教思想、学术水平令他无比兴奋,觉得“昨非而今是”,维新思想被他深深领悟。这成了他政治人生中的一个起点。
陈独秀经过与维新人士的交往,觉得找到了正确的人生方向,从一个被动读经的少年变成了主动接受新学的康梁派。
1897年,德国在俄国的怂恿下,借口山东曹州府巨野县有两名德国传教士被人杀害,竟然武力进攻强占山东胶州湾,接着俄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列强乘虚而入,竞相瓜分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陈独秀“痛感时势日非,不堪设想”。与科举彻底决裂的他,悲从中来,读那些死书,能救亡图存吗?他整日伫立窗前,眺望那波涛汹涌向东流去的长江,思绪万千,心潮翻滚。“控制吴越”的重镇安庆,自古建都南京的朝廷,无一不把安庆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当年的太平军与清军,不是在这里进行了长达两年之久的浴血征战吗?陈玉成丢了安庆,沿江城市也相继失陷,3年之后,天京不就失陷了吗?若防止内乱,必据上游;若防止和抵抗外国侵略,必须加强下游的防务。他在康梁学说的启发下,伏案写起他的处女作《扬子江形势论略》来,他决意向政府献上一策。
他忧国忧民,向清朝政府详细论述了长江的自然地理、水文地理、军事地理、经济地理等方面的情况,从长江具备“防内乱,御外侮”的战略地位到如何设防以破解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侵略意图。真可谓战略上高瞻远瞩,战术上细致周密。他不到弱冠之年,激情四溢,写出宏篇,激扬文字如江水奔腾,爱国情怀苍天可鉴。为了在国民中宣传、扩大影响,他还将这篇文章自刻自印自发行。
他在《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中最后写道:
“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经满蒙,法伺黔贵,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权力。”
“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为此,他又强调:
“爱采旧闻旅话暨白人所论,管蠡所及,集成一片,略述沿江形势,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也。勉付梨灾,愿质诸海内同志,共抱杞忧者。”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