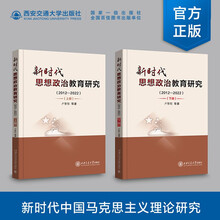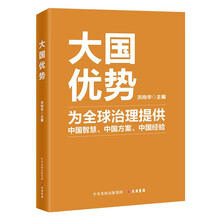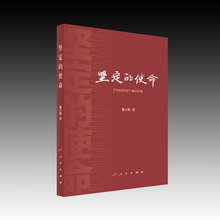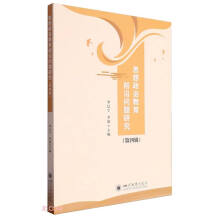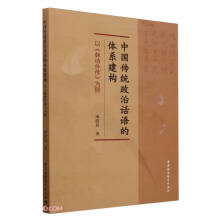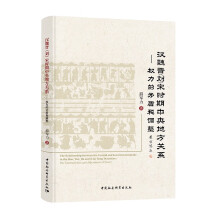《新时代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研究》:
当我们将问题引向这个方向的时候就回到了前面所讨论的现代自我的建构问题,它意味着在现代自我与至善(幸福)目的之间通过合德性的生命活动进行联结的可能,或者说,从现代自我的自身存在中可以牵引出遵循理性和德性生活的根据,因为自我的独特性中隐含着个体存在的幸福之根源,但它必须通过合德性的方式才能获得,即自我作为“本己的别具一格的能在”是其存在的动力和决心,以及其存在意义和幸福的源泉。因为真正的幸福不是动物式的快乐,也不仅是普遍意义上的类幸福,而是具体的、独特的,所以,当我们谈论幸福的时候只谈人类的幸福是不够的,而必须深入个体或自我的独特性中去谈论幸福,即使是现代个人主义者或许也不会反对这一点。因此,虽然每个个体或自我都寻求幸福的目的,但是获得幸福的方式,或者说,实现幸福的具体的生命活动是各具特色的,这些各具特色的生命实现活动发挥着作为人的存在的诸种功能性作用,而作为个体存在其功能性发挥的状况正是其存在的确证和意义的注脚,如果去除人的功能性的意义,无异于取消了人生命特有的活动(一般意义上和特殊意义上),同时也取消了获得幸福的前提和存在的意义。这种作为个体存在的功能性并非抽象的,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社会角色或身份构成,而作为人的好坏就体现于对这些具体角色的扮演中,同样作为人的快乐或痛苦也生发于对这些具体角色的体验中。至此,我们推导出人的至善目的与个体的独特性存在、生命的实现活动和人的功能性之间的内在关联。但需要继续思考的是,在个体或自我的各种生命活动中实现自身独特能在的生命活动与其他生命活动之间是何种关系?或者说,个体或自我应当如何处置自身所扮演的各种角色和身份(包括努力成为的)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在其所有的具体的生命活动中德性必须一以贯之、不可背离?
作为社会中的个体,包含两种功能性的意义:一是作为一般意义的好人即道德之人。他以至善为目的,不仅拥有德性,而且将德性运用于各种生命活动中,即好人既拥有德性同时又做得好,因此,好人的幸福是在合德性的实现活动中获得,同时,因为好人既合德性又做得好,所以,好人存在的事实又促进了他者和社会的幸福,或者说,相对于类的幸福好人发挥了好的功能。二是体现自身独特性的卓越之人或优秀之人(这种卓越更多是相对意义上的)。作为卓越之人或优秀之人,在根本上从属于好人,即是好人在其某种具体实现活动中因出色的表现而成为杰出之人。一般是在个体的自我独特的能在中去实现的,或者说,是自我的爱好和天赋得以在活动中充分地发展和实现。从功能性来看,是个体的某项具体活动发挥了好的功能,不仅是个体在别具一格的能在的实现中获得了幸福,而且也是个体以其特有的本质力量促进了类生活的丰富和卓越。正如,我们不会去说一个巨骗、大盗或毒枭是卓越之人,因为他们的特质对类生活的幸福形成了威胁和破坏。因此,好人包含了成为卓越之人的可能,而卓越之人本身就包含着对类生活的特殊的贡献。但有时好人也可能会影响其自身成为卓越之人,无论是一般意义上,还是特殊意义上,这种功能性意义的实现都对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现实身份或渴望成为的身份,对于个体存在者来说,每一种选择都包含了对自我的各种角色的权衡,大多数人也能承担起选择所带来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那些为了某种天赋的发展而一开始就选择独身的人,或是在取得个人成就后而回归家庭生活的人,或是为了某种神圣的事业而歉疚于家庭角色的人,不仅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值得尊敬的,因为在他(她)的选择中包含了对诸多责任间冲突的考量,在这种考量中体现出一个好人的受限与困惑,相反,一个缺乏德性的人总是会为责任的逃脱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
如果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好人”与“卓越之人”是内在统一的,那么,在现代社会好人与卓越之人常常体现为一种分裂的状态,如果拉入当代的中国社会,它表现为成为“道德之人”与成为“成功之人”的背离,在诸种生命活动中,或是在不同角色的扮演中,在有传统思想的人那里一般表现为对道德之人的追求,他们为了成为道德之人更可能会选择放弃自我的发展。而对稍后的和新生代来说,由于竞争意识的日益增强和与此相应的生活经历在不断造就着越来越多的个人主义的信奉者,对于正在形成中或已经形成的个人主义者来说,他者对于自我的存在而言更具有对手的意味,所以,在执着于追求自我成功的过程中,成为“道德之人”的实现活动就会被相对忽视。“企业家的身体里应当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这句话正是对这一现象的劝导。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