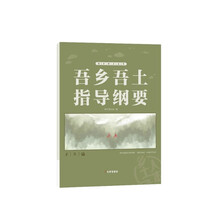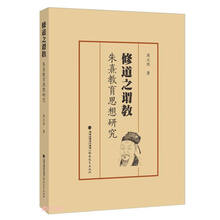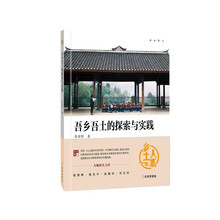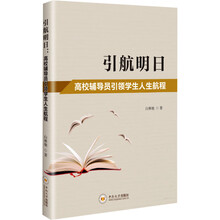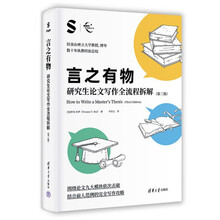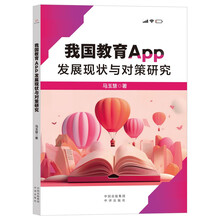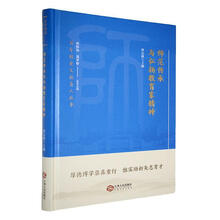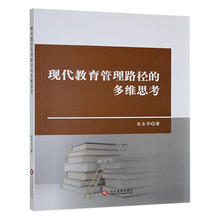《道德新说》:
这并不是说不应该重视典型或经验,而是说如此重要的工作,单单靠典型或经验来指导,显然是不合适的。当然,我本人并不谙于教育理论,或者说我的理论根基原本就十分薄弱。因此,尽管我十分努力了,但常常愿望是一回事,实际结果又是另外一回事。这犹如一个初学画画的人,他本想画一匹奔腾的骏马,但其结果很可能是似驴似马或非驴非马。我也一样,我原本是想从理论上把道德教育的有关问题说清楚,但因根基浅薄,不仅理论上可能没说清楚,而且可能还和广大的基层教育工作者的需要背道而驰了。他们需要的,我这里几乎没有;他们不需要的,我在这里哕里哕唆地说了一大堆。但这也实在没有办法,因为这原本就是我的初衷,我原本就没想介绍那么多的案例或经验。对此,我深信广大基层教育工作者,一定会理解并原谅我。其次,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而人是自然界最有灵性的生命体或如苟子所言:“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也就是说,人是自然界中最为尊贵的。人之所以“最为天下贵”,就在于人不仅有肉体,还有灵魂。因此,对于入的培养我们很难制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十分具体的方法。特别是有关人的私德的教育,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人的行为如何,更为重要的是人的情感、人的心灵。而人的情感只能靠情感去沟通,人的心灵只能靠心灵去启迪。或者说,教育原本就是情感与情感的交流、心灵与心灵的碰撞,人格与人格的相互影响。没了情感的交流,没了心灵的碰撞,没了人格的影响,哪里还有什么教育?而要想把人情感与情感的交流,心灵与心灵的相互沟通和启迪,都能用一套东西固定下来,变成程序式的、可以操作的具体方法,这在实践中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学校原本就无处没有教育,教师所讲授的每一节课中都有教育,教师的一言一行,甚至是着装打扮,对学生来说都是教育,我们不可能将每一件事情都做出详细的规定。因此,我们必须承认,道德教育不一定无法,但肯定没有定法。一些基层的教育工作者,他们期望能有一套现成的、具体保守,常常做不到位。子贡听到孔子如此评价这两位弟子,他以为老师比较肯定子张,所以问:“然则师愈与?”其意思是,这样说来子张更好一点儿?孔子却说:“过犹不及。”即做事做过了头和做不到位是一样的,并非做过了头比做不到位更好。言外之意,孔子主张做事要中道,即既无过也无不及,要恰到好处。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两端即两头或两极,代表矛盾的两个方面。在孔子看来,研究任何问题都要从问题的两个方面人手,即要“叩其两端”,不能只“叩”其一端。“叩”即敲,在这里是推敲的意思,“叩其两端”,就是要全面考虑问题,既防止片面,又反对偏激,只有“叩其两端”才能做到既无过又无不及,取其“中行而与之”(《论语·子路》),这又叫“执中”或“执两用中”(执其两端而用于中)。
《论语》中记录孔子信奉中庸哲学的例子还有很多,中庸明明是个方法论的问题,但孔子将中庸视为做人的道德问题,而且还说中庸是人的至德,甚至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其意思是,人有智慧可以治理好国家、天下,人有仁德可以辞去高官厚禄,人若勇敢可以上刀山下火海,但做到中庸是不可能的!可见,在孔子看来中庸之道远非五常之道可比,也绝非一般的道德。中庸为什么被称为至德呢?为什么连孔子都哀叹“民鲜久矣”,甚至“中庸不可能也”?这是因为除了圣人,一般人大都有私心和私欲,这些私心和私欲有的源自先天,有的源自后天。正因为有私心和私欲,做事就不可能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即使是在一件事上、十件事上都能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但要做到处处如此、时时如此,那的确是不可能的。时时处处都做到“执中”,甚至“时中”,那是只有圣人才能做到的事。子思说只有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一般人能做到“择善而固执之”(以上均引自《中庸》)就不错了,可见中庸是圣人之德,而五常之道则是君子之德。圣人是人们理想中具有最高人格的人,现实生活中又有谁见过圣人呢?但这并不等于说人不需要按中庸的要求去努力。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