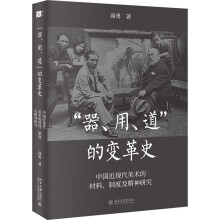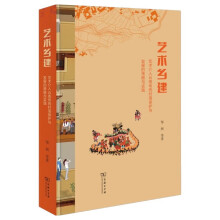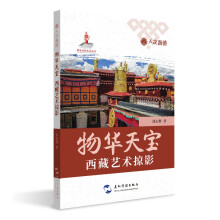《艺术与此在:论艺丛札》:
如果说只在《孔雀》里找到一些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符号性事物,那些西红柿、玻璃白菜、大白兔奶糖,确实是有意为之。但电影应该是且尤其应该是这样子的:它要再现时代的氛围,就不可或缺地要将彼时代的事物呈现出来,不管给我们的感觉是不是刻意的,它对此的塑造总算是可以达到本来设想的目的。
如果说只在《孔雀》里找到了些怀旧式体验,我只能抱歉地说你在进入它的同时将自己的个性消灭湮没掉了。因为这里是这样一种情况,二三十年前发生的事对于我们而言虽说陌生,但也只不过是二三十年前的事。如果不深究造成这种历史空白的原因,自然就是对现状的一种妥协。而妥协,正是《孔雀》真正的深层主题。
在电影看似杂乱纷扰的情节里,隐匿的阶梯性排列尤其让人难以察觉。《孔雀》中的三段论阶梯式排列正是典型的探寻问题答案的模式。
理想主义者姐姐算是最接近“孔雀开屏”的角色了。她在梦想碾碎的过程中有过几次奋力的反击与现实的自慰。她可以任由开水壶吱吱叫着而兀自拉自己的手风琴,她在托儿所里不安分的工作态度正是她对成为一只真正的孔雀的希冀而与现实的对抗。诚然,打开降落伞是有一种开屏的快感,但这种快感只是以牺牲为代价的自我安慰。这种对美丽的期许也只是现实中的梦终将破灭。文工团的老演员的不得志,是电影中少有的几次对电影发生时代及更上溯时代的追忆,是怜悯和同情,是压抑得透不过气来的时代在人身上最为痛楚的烙印。姐姐的最终妥协是在一次隐忍的痛哭之后,在遇见自己年轻时暗恋的英武军人,并且看到他那副携妻带子被折磨得早已是猥琐不堪的样子时,那种对理想、对爱情寂灭的哭泣可以很自然地在买西红柿时完成。而这之后,她才可以非常安静地随便结个婚,过上一种忘却的生活。总而言之,从对理想实现的希望和对现实的不满,以及对生活的抗争和对开屏的欲望上讲,姐姐是与时代和现实有过直接交锋的人物。
哥哥并不是个傻子,可是在现实中,他被当成一个弱智低能来对待。他从来没有想过去打破这种烙印,是因为他可以从中得到好处。他可以分到更多的糖果,在洗澡的时候可以躺着、眯眼笑着让弟弟帮自己脱裤子,而且可以自愿地受骗从而存下香烟。同样,他也可以得到母亲更多的疼爱。他虽然表面上认同周围人的看法,但实际上他对证明自己的能力,也就是在自我实现的欲望方面是最强的。他对比自己还要弱小的事物有一种普遍的爱心,比如那两只白鹅,它们不知道他的弱智,它们和他非常平等,所以哥哥愿意将少之又少的奶糖分给它们吃。哥哥有一种积蓄的冲动,他和样子难看的妻子相互认同,正是在自强这一点上。所以他们可以一起干活赚钱,他们有自己的梦要去实现。哥哥对“开屏”的最显著的渴望当然是对一个风骚女工的爱慕,但很快就破灭的这段感情没有给他留下太多的后遗症。他懂得保护自己。在得知那个女工因为没有生育能力而被别人抛弃的时候,他心里多少得到了一些慰藉。哥哥和他的瘸腿老婆在一种认同的状态中过着本分的生活。哥哥的认同是一种自我保护,因为他同时可以过着一种默默实现理想、永不满足的生活。他永远不会开屏,但他永远都会是一个胜利者。这种胜利表现为对现实妥协的勤奋。这与弟弟大不相同。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