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视觉政体:视觉现代性读本》:
在爱森斯坦看来,诸如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等宏大问题,都能在对出版商和印刷机的研究中得到重新认识。为什么她能给这种旧的解释赋予新的生命,因为她关注的不只是图形主义,更是图形主义中与流动性过程相连接的变化。例如,她解释了从印刷机的发明到真正出现逼真图画之间的延迟时间这一奇怪现象(p.508,参考了Ivins,1953)。一开始,印刷只是简单地被用作复制药草学、解剖图、地图、宇宙学等当时被人认为虽然古老但不够准确的东西。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符号层面,这些现象会令人迷惑不解,但当我们看到它们的深层结构时,就容易解释了。首先出现的是很多不变的流动体被置换,旧的文本传播到世界各地,人们可以在其他地方轻易地获取。随后,它们之间最本质层面的矛盾终于得以凸显。这些文本高度集中的地方会出现许多反例(不同的花、有着不同名字的不同器官、海岸线的不同形状、不同货币的不同汇率、不同的法律)。这些反例被添加到旧的文本中,并不加修正地传播到其他环境,在那里进行又一轮的比较过程。换言之,错误被不断累积,并被不加修正地传播开去。同时,修正也在快速增长,轻易且不加改变。最后,精确度从原来的媒介变成了消息,从印刷的书籍变成了建立双向联系的语境。一种对于“真理”的新兴趣并非来自一种新视角,而是来自旧视角,只是将其投射到在不同时空中流动的新客体。
爱森斯坦观点的影响在于,把心灵主义者的解释转变为不变的流动体的历史。她反复强调印刷出现之前知识界获得的每个成就——合理有序的怀疑主义、科学方法、辩驳、数据收集、理论构建等,人们都已经在所有科目(地理学、宇宙学、动力学、医学、动力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中做过了一切尝试。但每个成就都停留在此地和此刻,因为没有办法把他们的成果带到其他地方,或者不产生错误地介绍给其他人。例如,每个精心修正的版本在经过几次拷贝之后都会出现瑕疵。不存在不可逆的收益,所以不可能有大规模长期的资本化。印刷机没有给思想、科学方法或大脑添加任何东西。它只是无条件地保存和传播,不论对象有多么错误、奇怪或者粗野。它让一切流动起来,但这种流动性并不能抵消瑕疵侵入。爱森斯坦认为,新的科学家、牧师、商人、王子跟旧的没什么不同,但他们现在看到的是带有大量其他时空印痕的新材料。不管这些印痕最初有多么不准确,最终都会变得准确,变成更多流动性和更多不变性的产物。一种机制的产生即是为了捕捉准确性。印刷扮演的角色就像是麦斯威尔(Maxwell)的魔鬼。没有什么新理论、新世界观、新精神是解释资本主义、革新和科学时所必需的,它们不过是不变的流动体漫长历史中新阶段的产物。
埃文斯的观点认为,穆可伊(Mukerji)和爱森斯坦都重新关注插图书籍。对这两位作者来说,一旦图像被印刷,麦克卢汉所谓的革命就已经发生了。工程学、植物学、建筑学、数学,所有这些学科都无法仅仅靠文本来说清它们要谈的内容,它们需要用图画来展示。这种展示极为关键,然而在发明“成形的图像”(graven image)之前是不可能做到的。文本的复制过程中可能被掺假,但图表、解剖图或地图却不可能。作者给读者提供文本的同时,如果能提供大量所谈论事情的其他东西,那么,读者就能掌握解释的效果。假设所有作者和读者都这么做,一个新世界就会从旧世界中诞生,而无须任何附加条件。为什么?因为反对者也必须做与其对手相同的事情。换言之,为了“提出质疑”,他必须写另一本书,附带他要反对内容的反例铜版,并将其印刷出来。反对的成本将会增加。
如果有人能在一点集合大量可移动的、可读的、可见的资源支持一个观点,就能形成正面反馈。第谷提出观点后(Eisenstein,1979),反对者必须要么放弃和接受宇宙学家认为这是个无可争议的事实,要么提供反证说服王子为天文台赞助类似数额的资金。因为反馈机制是一样的,于是“证据竞赛”就类似于军备竞赛了。一旦一个竞争者开始建立更加令人信服的事实,其他人要么也这么做,要么投降。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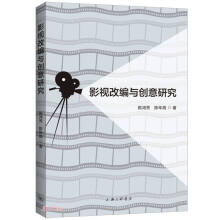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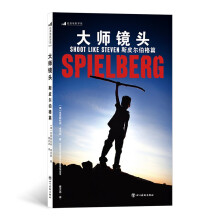
——马丁·杰
★一个世纪以来,早期电影的研究者们已经将那段时期的图景,从看作过渡到成熟电影形式(经典好莱坞电影以及它国际间的竞争对手)的一个序章或者革命性的垫脚石,转变为把它看作一种拥有自己的特性的电影,一种不同的电影。这种转变产生了关于早期电影传播与接受模式的细化研究,也包括了对电影生产一展映一接收环节的不同标准模式的研究。同时,它也使研究的重点从一个范围较窄的学术领域,转变为对现代性采用交叉学科式的研究,其目的在于在一个更大的领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转变——中来确定电影在其中的位置。
——米莲姆·汉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