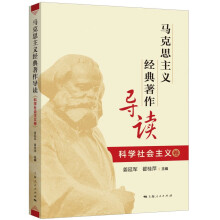《越界: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克里斯蒂娃哲学》:
在苏俄教科书体系中,“物”指的是抽象物质实体。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这种物,它只是人在头脑中臆想出的观念。这种阐释是前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唯物主义的翻版。
接受过拉康主义精神分析洗礼的新生代马克思主义学者齐泽克、巴迪欧、梅亚苏重新诠释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他们提出“物”是一种“真实的剩余”。用拉康的语言学来表述,它是能指链上发生的裂缝。正因为这道裂缝发生在能指链上,因而无法用言语描述它,只能用视差之见来觉察它的存在或是用症候来掩盖它的存在。
回到克里斯蒂娃那里,她显然不同意苏俄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对“物”的理解。同时我认为她也不会赞同齐泽克等人对“物”进行的拉康式的语言学化的处理。一方面,她把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看成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生物学版,或者说是一种“身体唯物主义”。①另一方面,她把自己在弗洛伊德启发下创立的符号概念也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这种由驱力激发的符号既带有生物学的某些痕迹,同时它又是诗性语言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它也名正言顺地成为一个语言学的范畴。可见,她的“物”介于弗洛伊德的身体唯物主义与后现代的新辩证唯物主义之间。似乎可以这样猜测,克里斯蒂娃在其中发挥了某种桥梁的作用,只有经过她的“符号”才能从弗洛伊德的驱力走向齐泽克等人的“真实的剩余”。
出于她对“物”的理解,克里斯蒂娃把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法来解读否定性的做法视为一种唯物化处理。这种处理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在发生学上理顺判断内的否定和先于判断的排斥之间的逻辑关系。
弗洛伊德在1925年的一篇题为《论否定》的论文中指出主体的判断分两种类型,一种是肯定或否定对象的某种性质,如好的/坏的,有用的/无用的。只有好的和有用的东西才能进入自我。另一种是肯定或否定对象在现实中的表象,如主观的(不存在于现实中)/客观的(存在于现实中的)。因此对于意识而言,满足需求的对象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它既要具备能够进入自我的“好”的性质,也要实存于外部世界,一旦需要即可再现和摄取。①他指出,人最基本的思维能力就是关于这两个条件的判断。对于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东西,可以进入意识,可以被象征化为语言符号;而对于不能满足条件的东西,主体先是在无意识中压抑它,然后逐渐演变为用否定来有意识地拒绝它,也就是说此时“对自我中无意识的承认是用否定的形式表示的”②。这种否定的思维能力与单词句的习得是同步的,大约发生在幼儿15个月大的时候。这就印证了弗雷格的一个洞见,即“内在于判断中的否定是象征性功能和/或句法功能的标志”③。幼儿能够说“不”就等于他已经知道如何在句法上形成有指向的句子,尽管只是一个最低级的单词句。
这种判断力的出现与象征语言习得的三阶段——镜像、阉割和设定阶段同步。可以这样理解,否定的判断能力与象征语言能力的发展过程是同构的,一个言说主体即是一个理性主体。并且,这个主体的判断和语言能力都依赖于在镜像和阉割阶段发生的两场分离,即自我与外界以及自我与母亲的分离。换言之,分离是理性判断和象征语言这两种能力产生的前提。
克里斯蒂娃关心的问题是符号语言的习得是否也需要经历一场分离呢。她在弗洛伊德写于1922年的《超越快乐原则》中找到了答案。他发现判断的两极性(好与坏,存在与不存在)并非人的先验能力,而是发端于两种性质相异的本能冲动。肯定判断来自生命驱力(即求生本能),为了个体生命的延续,身体本能地吸收所有好的、有用的和在现实中可获取的对象;否定判断来自死亡驱力(即求死本能),这是他尤为关心的东西,因为这种死亡驱力正是否定性的唯物主义版本。在临床治疗中屡次发现的移情现象促使他得出以下结论:人受制于一种强迫重复症,它是生物始源性的惰性表现,它不仅要求重复以前的经历,尤其是诱发创伤的不幸经历,更是要求回复到生命体最初的无机状态。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