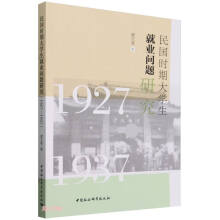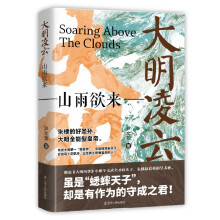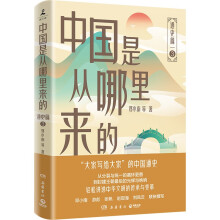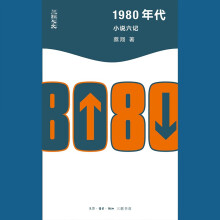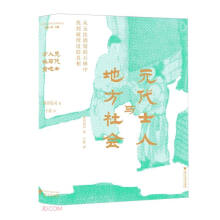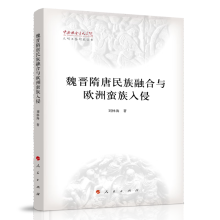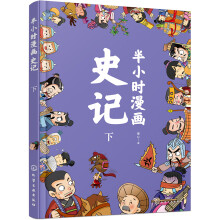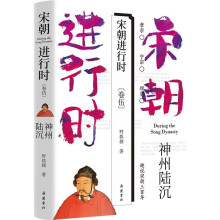感悟教育人生
——重读《荆棘之路》
陈君实
2002年5月,承蒙当年几位同仁和学生,在我从教五十周年的日子里,编辑、出版了《荆棘之路——陈君实教育实践文集》。福州一中为此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福建日报》、福州电视台等媒体也做了报道。从那以后时间又过去数年,我已步入耄耋之年,但我仍在思索着当年的办学和这本书的内容。感到仍有些许心得,写了下来,借贵刊一角,以发老凤之声,为当年教育教学工作做一总结。
我在民国时期接受了比较完整的学校教育。小学、中学各上了六年,然后通过联考进入大学经济学系。经过四年的学习,做完毕业论文,获得学位。在大学期间,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反对蒋介石政权的学生运动和闽西南游击区的武装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在闽北农村做土地改革工作,组织农民分田分地。1952年6月,奉召到福州报到,为福建省第一批派校干部。当年8月底,受命到福州一中任副校长,负责教学和行政工作。1956年起任校长(后又兼党支部书记)。1959年被调离。1962年夏,返校继续任校长。“文化大革命”时期,再次被撤职。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再返校接任书记兼校长,直至1983年调省教育厅。
中学本来应当是风平帆直、细雨润物的育人场所,却逢多事之秋,让我的个人遭遇起伏跌看、曲折万分,出现“三进三出”福州一中的奇特经历。
但是,我之所以称当年的创业和不懈追求的历程为“荆棘之路”,不是从我个人经历着眼。同党的伟业比较起来,个人的牺牲算不了什么。我仅从技术层面和人文层面来说明当年艰辛曲折的探索创新之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举,我们接收了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各类学校,并加以调整改造,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人民学校。但是,这性质全新的人民学校究竟是何样的规制与模式,则没有现成的依据,只能靠人们在实践中探求,逐步建构、充实起来。而在这一全新的探求中,除了上级的正确指示之外,校长(或书记)个人的教育素养是起着很大作用的。可以这么说,我当年是凭着自己在求学中积淀的“教育直觉”和“教育良知”开始了我的教育生涯。
比如,当时强调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在改造旧学校、建设新学校的工作中,也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那么,在一所中学里,该如何举步,才算是贯彻了这条路线?我很快意识到,最为基本的是发动、组织教师队伍,依靠他们办好学校。因为只有他们才是内行、专家,才是学校的稳定力量。有了这一基本认识,我就不避当时的忌讳和风险,对校内从旧社会过来的教职员,从人格上尊重他们,业务上信任他们,生活上关心他们。同他们平等沟通,展开对教材内容的研究、切磋,对教学形式的互动研讨,同他们建立起互动互信的关系。我坚持深入课堂听课,了解不同教师的不同教学风格,做到心中有数,让校长不但到岗,而且到位。所以,尽管当时有些外来的干扰,但是由于有了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福州一中很快形成了稳定的教学秩序,浓厚的教研风气,和谐的进取步调,为学校后来的质量全面跃升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到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①。后来又加上诸如“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等“限定”,教育界立即掀起学习贯彻的热潮,与此同时,也提出向苏联学习,引进凯洛夫教育学。在学习、实践、思索中,我对党的教育方针的理解,着重于两个支撑点:“全面发展”和“生产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在未来的新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我理解人的“自由发展”,必然是人潜能的充分的、全面的、多元的发展。《共产党宣言》又提出要“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所以党的教育方针中的两个支撑点,是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在我国基础教育中的具体体现。我的所谓治校方略,主要都是围绕着两个方面展开的,坚持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协调发展,不可或缺;坚持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接触社会实际,这对学生形成正确的思维方法,良好的进取心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必由之路,必须列入计划,持之以恒。在这些观念的支配下,我们建立起以课堂教学为中心、配以充分的实验设施的教学体制,校内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教育模式,建立了雷打不动的“三表”制度,大力提倡深入理解教材,充分发挥教材资源,以拓展提高学生分析能力为宗旨的课堂教学风格。由此,我们获得了规律性的认识,因此成就了连续三年“高考红旗”辉煌业绩,奠定了福州一中在中学界的领先地位。所有这一切,在《荆棘之路》中都有较为详细的总结与记述。所以,从具体的技术层面看,我们白手起家,潜心研讨,付出了代价,也获得了宝贵经验。正如《荆棘之路》编委会在首发式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