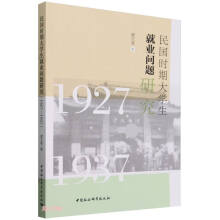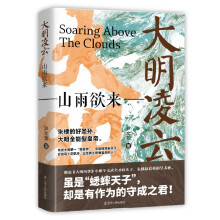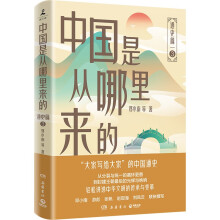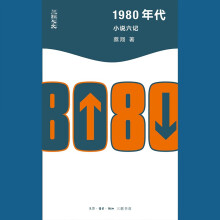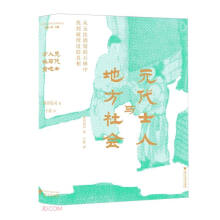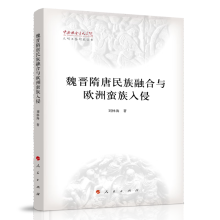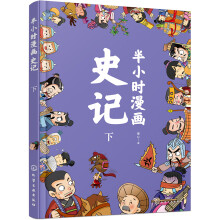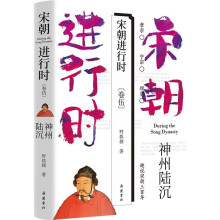《安里村往事:胶东一个乡村的记忆》:
鬼子来了
1940年冬季的一天,那一天好像是冬至,家家户户正都忙着包包子,突然听到飞机的声音,是日本鬼子的飞机来轰炸姜疃,因为姜疃有抗日民主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很多人从家里跑出来看,首先飞来的是单翅的,人们都说是侦察机,紧接着又来的是双翅的,人们说是轰炸机,我们都叫它“飞艇”。当轰炸机往下扔炸弹时,有的人看着说:“快看,飞艇拉屎了。”还有的人说:“快看呢,飞艇下蛋了。”炸弹落地以后,爆炸声很大,吓得人们东躲西藏,再也不敢看热闹了。没过几天,又来轰炸了两次。
自从炸了姜疃以后,日本兵和“二鬼子”(汉奸、伪军)隔三岔五地来安里村扫荡。进村以后,不是拉驴牵羊,就是抓鸡抓狗,无恶不作。有一次,他们进村抢了很多东西,“二鬼子”用担子挑着往西走,快走到姜疃的时候碰上盖功存(盖信和盖强的父亲),他们就叫盖功存给挑着担子,送到崔疃河东岸时放他回来了。一个“二鬼子”还给了他两个小钢钱(当时使用的一种钱币)。
第二年春天,张维恒(张玉友、张玉朋、张玉杰的父亲)在牵人沟坝头那里剜苗儿,被扫荡的日本鬼子看见了,叫他,他也听不懂,因为害怕,爬起来就跑,日本鬼子举起枪来就打,他被打伤跑不动了,日本鬼子过来用刺刀把张维恒给活活刺死了。那一天,我们几个人正好就在出儿山前兰家坟南,眼看着这一幕惨剧,害怕极了,大气都不敢出。(韩仁贵)
闹蝗灾
1944年立秋到处暑这段时间,安里遭受过蝗灾。据说是从日照那边飞过来的,持续了二十多天。每天下午从两三点钟到五六点钟,一群一群的蝗虫遮住了天,掠过安里村和上夼村往东飞去,大部分都落在宋母顶以东、东南山和河子山沟以北这些地方。我记得,天不亮的时候,就有很多邻居起来一块儿去捉蚂蚱。天刚开始露白是捉蚂蚱的最佳时机,一是蚂蚱的翅膀沾了露水飞不起来,二是蚂蚱冻了一宿不大能动弹。我们趴在地堰下观察四周,只见谷子地、高粱地和山草堰上最多。伸手握着作物的秸秆往上一撸就是一把,装在布袋子里,接着再撸,一早晨能捉一袋子呢。等到太阳出来,蚂蚱就不好捉了,见人就飞。
蚂蚱拿回家以后,不敢直接解开袋子口,怕它们飞了。一般是把袋子放在铁锅里的锅卡权上,添上水烧火蒸,然后从布袋子里把蚂蚱倒出来,用热盐水焯熟就可以吃了:抓过一把,拿出一个,用手把蚂蚱头轻轻一扭往外一拽,头和肠子不要,再把翅膀一扯,剩下身子就着饭吃。记得那年过中秋节,过节菜全是用蚂蚱做的。开头几天还觉得挺好吃的,后来嘴都吃出口疮来了,妈妈就把吃剩下的蚂蚱用水磨磨成了蚂蚱酱,足足两大坛子,留着来年春天吃。
1945年春季安里村解放后,上级号召各家各户不分男女老少都要上山消灭蚂蚱幼虫。男劳力拿着铁锨在地里挖沟,妇女儿童每人拿着一根树条,往挖好的沟里驱赶蚂蚱,后面紧跟着的男劳力用铁锨往沟里填土压紧,连续忙活了十几天。(韩仁贵)
盖万与一支枪
盖万家住上疃小北山顶,通往他家的陡坡路面都是麻岩石,凹凸不平,十分难走。他贫农出身,长得人高马大,加上身体健壮,早早就加入了民兵组织。他积极参加站岗夜巡、支前等活动,在给村里的军烈属代耕时,大家也都争着选他。
1947年前后,解放军一支队伍行军途经安里村。走到盖万屋后时已近午夜,天上阴云密布,道路漆黑一片。一些来自平原地区的战士,从小走惯了平道,加上又是夜里,走不惯乱石遍布、坎坷不平的山路。盖万夫妻俩知道后,急忙往油灯里加上仅有的花生油,挑高灯芯,打着灯笼赶上去为队伍照明带路、提示路况,盖万还让妻子回家提水给战士解渴。分别时,部队首长拉着盖万的手,再三感谢。并记下了盖万的名字。
事过月余,村里接到上级发来的一面“拥军模范”锦旗和一支崭新的步枪,指名奖给盖万。从此盖万只要参加民兵组织的活动,就背着那支擦得锃光瓦亮的步枪,十分荣耀。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凡村里在西学校放电影,盖万的长子盖好云就背着那支枪进场维护秩序,成为当时村里的一景。(张正齐)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