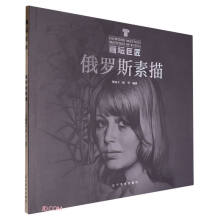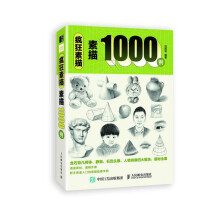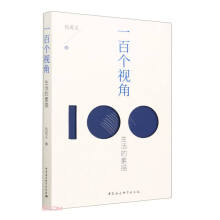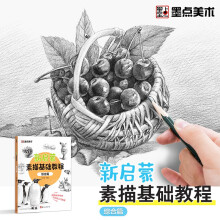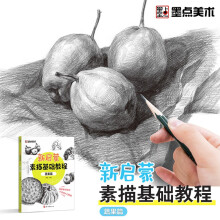美育始于家庭
回忆我的素描之路,当从家庭的启蒙教育开始。父亲14岁前到北京大栅栏天宝金店做学徒工,曾为中医的伯父郭兆钧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据说在我3岁时,伯父已教会了我认念很多方块字,大多为与中草药有关的单字。汉字是由线条组合成形态不一的方块字,且有音与义的不同,称之为抽象艺术亦无不可。据长辈说,在我已认念300余字时,因怕我累心便停止了这种识字教育。可能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即在我出生前还有两个哥哥均未保住生命。我到6岁时,才开始入村私塾念书,先拜一个木牌位,直书五个字为“天地君亲师”,继从《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的顺序认字念书。与此同时,每天要接触笔墨纸砚,先从描红开始,红模字为木版印成的红字,如诗的内容:“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将描字与诗、数一起结合学习,既全面又印象深刻。描到一定的程度,初步熟悉了运用毛笔按提力度的变化规律,我便开始临帖了。I临帖要用自制的大仿本,制作大仿本是一项手艺活,即将大张的元书纸经过裁叠成册,再用圆锥、纸捻穿连固定。通过自制的大仿本,熟悉工具与纸材的性能,这也是一堂手工课的实习。临帖从柳公权字帖开始临摹,所需字帖、笔墨材料由流动的书倌到各村提供。这种描红与临摹的学习,对于培养我后来持各种笔的造型写生能力起到先期的基础作用。
我的母亲也是我的启蒙者。在我四五岁时,母亲买了一张贴在坑围上的年画,是图文并茂的连环图画,它印在一张纸上,故事内容为“狸猫换太子”,说的是北宋时期发生在宫廷的历史故事。文图对照将内容人物识别出来,这也是知史的起步,同时我开始知道古人就有正、反两方。
我的母亲虽不识字,但会绣花,一般的针线活更是“多面手”。我穿母亲做的布鞋,从鞋帮到鞋底都是她一针一线地缝制的。有时她在绣花时,也给我一块布,并教我怎样索成一条线。这种一针一线认真做事的精神,是一种心性的磨练,也应是一种人生态度。
入读昌平县立小学
1940年,我8岁时为避农村匪患,便随母亲、三嫂、表兄一起从东营村迁到昌平县城居住,并入读昌平县立小学。我从一年级读起,表兄迁入四年级学习。我与表兄每日黎明即起,一同上学。学校每天早上先在校中集中开会,然后列队走到街南大操场跑步。六年级同学排头,我们排尾,队伍很长,前头跑小步,后头的一年级则跑大步,两年的晨操锻炼有利于我的健康成长。
我读县立小学一、二年级时,所幸的是刘秉琳老师担任班主任。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一位典型的师范学校毕业的女教师,身材略高,留短发,穿灰蓝色的旗袍。她上课重视汉字书写的笔顺,面向黑板写字的同时,还要求同学们大声跟着她喊出“横横竖横”,以增强书写的记忆力。
刘老师对我特别关注,还选派我参加县立举办的赛美会,事实上就是接受两位评审员的面试提问。刘老师有时还要我穿过小巷到鼓楼东街买东西,这也是一种锻炼。那时还安排一门唱游课,任课老师是郭兆民先生,在操场上,老师弹奏风琴,教大家边唱边表演歌词的内容。
我于10岁那年由昌平县立小学随母亲移居天津,人读私立卞氏小学,读三年级,这是一个家族办的学校。校长姓缪,在兄弟中排第二,人称缪二先生,其三弟、六弟、七弟均参与教学,也有外聘女教师一二人。有位邹先生为三年级班主任,布置课外作业是固定的每天要写一篇大仿(楷书)、三行小楷,大字临柳公权、小楷临《灵飞经》(钟大可书)。两年后,我改人天津市立第三小学,得见一位杨先生亲自示范临摹魏碑,应为杨大眼碑。笔画见方,不重复、不补笔,一笔到位。第三小学在城内东门里大街路南,路北有孔庙,正面外树有牌坊,上有匾额,东为“德配天地”,西为“功昭日月”,字体端庄大方。出东门内大街即东马路,附近有戏院,我曾观鲜灵霞主演的《人面桃花》评剧,男主角崔护的饰演者曾在四扇屏风上书写崔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行书字迹之大,在后排座位都清晰可见,足见演员之气度与功力。
东门附近还有青年会,常有些文化活动,我曾进去聆听戏剧作家洪深的一次关于戏剧的讲座,因年幼印象不深。另一次为黄二南的“舌画”示范,先吞墨汁,后以舌贴纸舔画,新奇显能,以舌濡墨,自然无锋颖之美。
天津是商业发达的城市,商场、商店的牌匾也是展示书艺的地方。如天津的繁华区有“劝业场”,即由华世奎所书,还有东北角的正兴德茶庄也是华氏所书。华世奎书写颜体字,在普及文化方面有较大的影响力,直到现在,走在天津大街上,所见招牌仍可屡见华氏的遗风。
我曾住天津南市药王庙街,现已改街名,为东西向的横街,东口通南北向的东兴大街,西通荣业大街,在街面或胡同口曾有租赁图书的书摊,也有租借连环图的小人书摊,我也曾是一些书摊的读者。
有一年,在东兴大街路东有一处书法地摊,除了有关福、禄、寿、喜等吉祥字外,还有一横幅,由右至左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