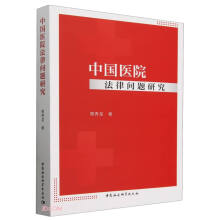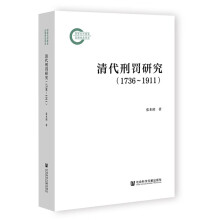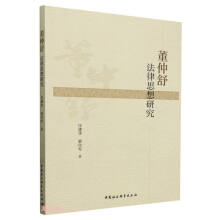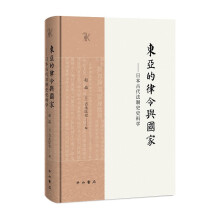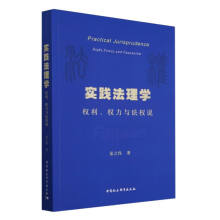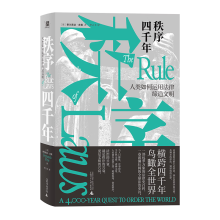《治官与治民:清代律例法研究》:
刘儒恒是本案我们特别关注的讼师。如果说任儒同完全没有是非,理应受到惩罚,然而与任儒同不同,正是讼师刘儒恒的介入,才使得三命之案得以转圜。梳理寿州案有几个关键环节,都是刘儒恒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才使得案件向事实依归,最后得到较公正的判决。一是寿州案发后一年有余,已经由原被双方“私下和息”。作为尸亲,张伦之兄张怀因为与张体文家本是同族,而张伦在张家做杂务,即得到张家的照顾,遂对张伦之死没有异议。李赓堂父子的尸亲李东阳已经拿到张家二千四百两银子,知州郑泰因没有按规定上详,有把柄在任手中,遂通过管门家人苏三也给李东阳五百两银子。至此,当事双方已经取得“平衡”。其后重新提起诉讼的是与尸亲没有关系、同姓不宗的李复春,而李复春的状子是刘儒恒所写(刘儒恒称他看过,这是讼师规避惩罚的通常做法),随即江督陈大文受理,并审出通奸谋毒。这是寿州案的第一个关节点。而陈大文之所以受理,是因为主要涉及知州郑泰匿案、书吏衙役通同舞弊。李复春的控状能够控准,这是需要借助讼师刘儒恒的“刀笔功夫”。铁保在奏报中称三命之案本是中蛇毒而死,无所谓通奸,是李复春“突出”,才有后来的“通奸”“谋毒”。
寿州案的第二个关节点是鄂云布诚轻情节,即没有改变因通奸谋毒的事实,但犯罪主体变为家长且已故的张体文,而包括郑泰在内的官员责任被“化小”,这是官府惯常的“化大案为小”的做法。此时,正是刘儒恒遣子刘荣先京控,并先在刑部审理,使得寿州案的更多情况在最高司法审判机构“备案”,同时也敦促此案的审理。其后最终判决的基本事实整体没有超出这份“备案”。此时如果没有刘儒恒一控,案件会以“温和”的方式结案,但真凶不会出现,张家名声虽有损失,但用的是张体文怀疑胡氏与张伦通奸而谋毒,至于是否真的有通奸之事,没有确定。同样,张家人受到一些惩罚,包括张体文的孙子,而他是未成年,可以通过纳赎解决。由于刘儒恒一控,刑部有了初审,请旨派新任总督复审。
寿州案的第三个关节点,也是惊天逆转的一次,是铁保的复审定案。这里本案至关重要的一个关节点,因为他颠覆了通奸、谋毒的陈大文之奏、鄂云布之初审。逆转的关键是抓到了讼师刘儒恒“诬告”。因此如前所述,铁保把案件偷题转换为“遵旨审明讼棍诬奸毙命重案核拟具奏事”,此次案件完全“平反”,而讼师刘儒恒成为主角,因为讼棍例不足以惩治,按凶恶棍徒例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而张大勋等前经陈大文奏准革除的举人要开复,“平反”昭雪的官员遇昌、周锷等要议叙。这也是寿州案发以来地方高官第一次正式的结案报告。此次刘儒恒成为被告,也成为最大的“输家”。刘儒恒当然不会接受,遂有遣妻第二次京控,也才有初彭龄之抚皖,才有寿州案回归真实,才有张家一死(张大有斩立决)、一遣(张大勋),才有被害人分得张家家产的经济补偿,才有多位大员遣发新疆。在初彭龄第一次奏报“大概情形”一折中,从叙事的逻辑关系中,已经非常清楚表明刘儒恒起到的正面作用。在叙述铁保“平反”前后与初彭龄抚皖的关联时称,“刘儒恒遣子刘荣先以减轻情节赴京呈告,奉旨饬交督臣铁保,审系烘板中毒身死,并非因奸谋命缘由核拟具奏”,“适刘儒恒之妻刘汪氏复赴都察院翻控,奏奉谕旨,交臣(初彭龄)审办”。嘉庆帝关于寿州案的第一次见诸实录的谕旨,也证明刘儒恒对寿州案的推动:谕军机大臣等:安徽寿州民人张伦、李赓堂、李小八孜三命中毒身死一案,前因屡控屡翻,交初彭龄审讯。这里的“屡控屡翻”,确切说,就是刘儒恒分别遣子、遣妻在都察院和步军统领的呈控。而作为被告的张家,以及原告李复春,在此前都没有京控。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