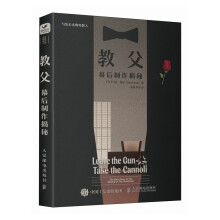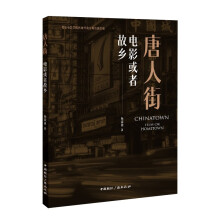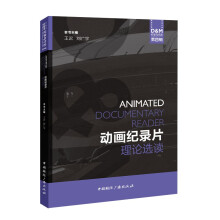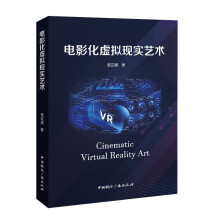《当柏拉图遇到卢米埃尔——电影中的哲学思辨》:
三、语言的遗忘和“大舌症”
虽然我是学院里面的一个局内人,但是我深深感觉到当代学院哲学在大众心目当中有两重形象:一方面,她被过于神圣化。但是它担负不起锤炼大众思维、塑造民族性格的重任。另外一方面,一些人会对哲学完全没有兴趣。因为在他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当中,哲学给他们的感觉就是无聊、死板、教条的。在这两种形象之间怎么找到一个平衡点?我希望通过这个课程找到一条“中道”——它既不是过于神圣化、被供奉起来的哲学,但也不是教科书式的琐碎、乏味的哲学。
当然想要切入这个“中道”非常难。即便是专业学哲学的人,也总要有一条路径通向哲学。有的人通过文学进入哲学,有的人通过科学,有的人通过政治,也有的人通过自己的人生体验进入哲学。可以说,但凡有一些悟性的话,条条大路都通往哲学。和不同的人谈话,他们对哲学的看法千差万别,态度迥异,但是谈到对电影的看法,几乎没有人说自己不喜欢看电影。仅有的差异在于喜欢看哪一类型的电影。我这门课用“电影中的哲学思辨”作为标题。前面不是主要的,关键是后面那一部分,这个主题是典型的偏正式的“钓鱼党”。
我现在每天读论文,读着比较烦。论文也是用拗口的学术语言来进行写作。所以我有时候想,哲学是不是得了一种病——大舌症。当代学院哲学说出来的话很少有人能听懂。这是学院哲学的一种遗忘,她遗忘了语言的丰富性。因为在哲学的开端处,并没有这种病。无论是在西方哲学那里还是在中国哲学那里,这种病都是很晚近才出现的。例如在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其实有三重形象:第一重形象是“精神的助产士”。他在雅典的广场上跟别人谈话。他会问这样的问题:快乐是什么?你认为快乐是什么,你给他一个答案。但当他连续追问三个问题之后,你多半就答不下去,或者说已经到思考的边界了。苏格拉底三天两头做这样的事情,可见当时的哲学是聊天式的,有时也有点论辩式,总之刨根究底,让你陷入两难,自己跟自己产生了矛盾。当别人反问他的时候,苏格拉底就回应一句:我知道我不知。苏格拉底的这种做派帮助了很多人,但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他最终因为毒害青少年和亵渎神灵而被判处死刑。他本来有机会逃走,但他还是选择了慷慨赴死。“助产士”也就是接生婆,帮人生小孩的。这是什么意思呢?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