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讲国学/传统文化经典教育文库》:
皮锡瑞经学历史把经学分成十个发展阶段,即开辟时代、流传时代、昌明时代、极盛时代、中衰时代、分立时代、统一时代、变古时代、积衰时代、复盛时代。其中两汉就经历了流传、昌明、极盛、中衰四个时期。皮氏是今文经学派,他认为孔子定“六经”开辟经学,孔子之前有书无经。例如《书》《诗》在孔子之前都有数千篇,但那不是经,因为微言大义不明。孑L子定《书》百篇,删《诗》成305篇,《诗》《书》才成为垂范万世的经书。这一点可商榷。实际上,即使孔子定成“六经”,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它们也不会成为经。秦以前,“六经”地位不佳,虽是显学,不过是儒、墨、法、道诸家中的一家。所以,经学开创由西汉始,没有汉王朝的支持,“六经”就不成其为经。
经学在西汉初始立。汉初定天下,百业待举,首要的是吸取秦二世败亡的教训,制定新的治国方略。汉高祖刘邦认为自己是在马上打天下,不信儒学。有谋臣劝他说,在马上打天下,并非可以在马上坐天下。叔孙通这个人对儒学复兴是有功的,他是秦博士,归汉以后,很识时务,顺着刘邦的心意,逐步启发刘邦对儒学的兴趣。他说,儒学虽不能进取,但可以守成。叔孙通按儒学制定的礼仪,刘邦果然很欣赏,任他为太子太傅,叔孙通的弟子也多被任官,这是儒学在汉复出的开始。惠帝、吕后时,公卿都是武力有功之臣,儒学未受重用。文帝时,有儒生稍有征用,并立《诗》经博士,但汉文帝本好刑名之学。景帝时不任用儒者,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儒学之士始终没受重用。
儒学的大翻身是在汉武帝时期。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春,立《诗》(文帝时已立)、《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武安侯田蚧为丞相,又罢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重用文学儒士,凡通五经之一者,都受俸禄为官,一些治经有成就者,更高居显位,如公孙弘因精通《春秋》升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
经学自西汉元帝、成帝至东汉,处极盛时期,全社会上下尚儒崇经成为风气。自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后,成为惯例,凡丞相必用精通经术者。公孙弘还建议,为弘扬经术,请为博士官设弟子50人,凡学经有成,都有任用,开中国明经取士之先。朝廷对这些因通经术而受任用的人给予极高的礼遇,不但任官,且免赋税。兴经学导以利禄,这是汉代推动经学发展的重要策略。自此,学习经学成为时尚,四海之内,学校如林,汉末太学学生达到了万余人,是从前从来没有过的。当时,社会上有这样的说法:“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
西汉重经学讲究实用,朝廷制礼仪,定治国政策,必引经据典;官员论辩,帝王论政,也必定引用经文,出口成章;凡议论,不引经便无以作据,不足信。不少人在日常生活中,也确实努力实践经教,并不浮于空泛议论。所谓经学极盛,这是重要标志之一。“经”不论从国家施政还是生活言行上,都是实践的准则,起行为规范作用。这其中似没什么学术性,实际是“有经无学”,经文已明,照着做就是了,对“经”本身不能再生议论,皮锡瑞称此为经学昌明纯正的表现。当时流行的经文,主要是由“焚书坑儒”劫后余生的耄耋儒生口授,用汉代通用的隶书写成,故称为“今文经”。
经学的今古文之争始于西汉。秦始皇坑儒,经书都在该烧之列,《易》按占筮书论,《孟子》按诸子书论,躲过秦火。其他如《诗》是口耳相授,焚书也奈何不得。汉初倡儒学,凡无字的“经”,方开始书于帛卷上,这就是“今文经”了。另外的被秘藏而躲过秦火的经书,例如《书》,则是先秦篆书书写。所以,汉初经书就有今古两种文字的版本。
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到一批先秦经书,自然都是古文,这与当时已存在用今文(隶书)书写的经书有同有异。孔安国得到这批书,用今文读之,并请求立博士,这便与已获认可并占据一统地位的今文经博士们发生冲突。西汉末刘歆极力要打破今文经的统治地位,力争古文经的地位。刘歆后来做了王莽的国师,助莽篡汉,古文经的名声也随之大坏。东汉时期,今古经已不是两种文字的异同问题,而是涉及如何解释经书的意义,出现经今文学派和经古文学派的对立。
由于以利禄作导向,两汉学经论经蔚然成风,皮锡瑞看出这极盛之中已隐含走向衰落的趋势。今文经占统治地位时,学经极重师徒传授统绪即师法、家法,论经者绝不能背叛师门家规。古文经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静,辩论经义已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开始出现对今文经的疑虑。有人认为今文经的风气不变,便难以经受古文经的诘难。于是,各种不同的经说纷纷萌生。其实,从经学发展过程看,这也是必然。就学术上说,也未必不是好事。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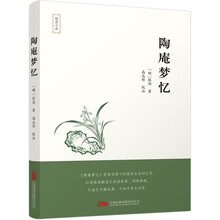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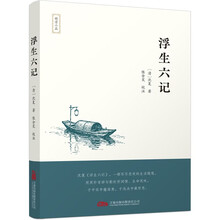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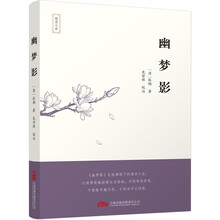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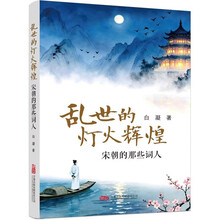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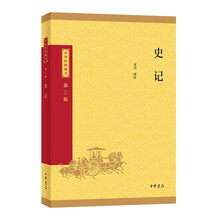


——《礼记·学记》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