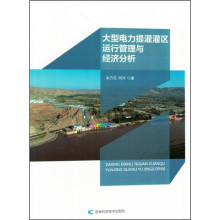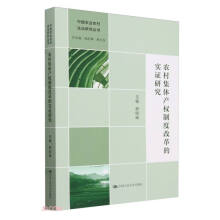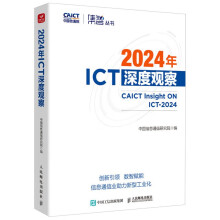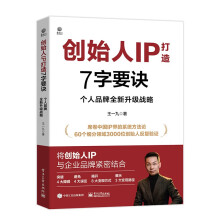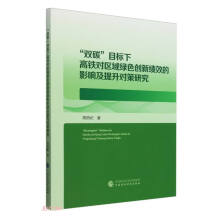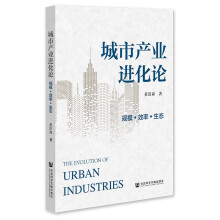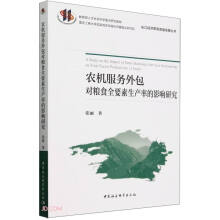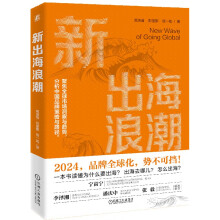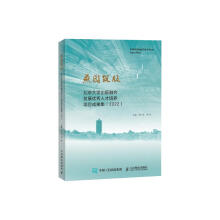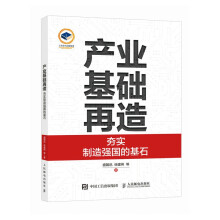第1章 绪论
1.1 背景简析及研究问题
1.1.1 背景简析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充分释放了农业生产力,使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30476.5万吨提高到2016年的61623.9万吨,年均增速达1.87%;农林牧渔总产值也从1978年的1397亿元增加至2014年的102226.09亿元,年均增幅高达12.66%。粮食产量的持续增长无疑为我国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然而,就种植收益来看,却显现出增产与增收不同步的问题。据统计,1996~2007年,除棉花和油料作物外,其他农产品的净收益均有所下降。三种主粮(水稻、小麦、玉米)的成本收益率也从1998年的44%下降到2009年的32.05%。有些农产品甚至出现了亏本(韩俊,2008)。诸多学者从时间成本(Wuetal.,2005)、生产成本(黄季焜和马恒运,2000;王秀清,2000;Wan and Cheng,2001)、生产效率(Fleisher and Liu,1992)等角度论证了我国土地细碎化经营是导致农产品生产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尤其是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到达刘易斯拐点后,农村劳动力不再无限供应(蔡昉,2008),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劳动力短缺进一步放大了土地细碎化的不利影响(吕挺等,2014)。传统经营模式面临土地细碎化、农户兼业化、劳动力弱质化、农业副业化和生产非粮化等问题(罗必良等,2012)。农村土地细碎化、经营规模小微化为特征的传统经营方式,不仅增加了农户的交易成本,而且使单个农户难以承担农业生产所面临的自然风险及农产品销售所面临的市场风险,极大地限制了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效益和农业专业化、集约化发展(温涛等,2015)。
因此,一直以来学术界和政界对于如何改变我国农业的分散化小规模经营格局,推进农地流转集中,提高农业生产效益都较为关注。国家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推动农地流转集中并实现规模经营,但是实施效果较微。就目前情况而言,我国农地的集中与规模经营短时间内很难成为基本趋势(罗必良等,2012),传统农户还是绝大多数,轰轰烈烈的其实都是一些典型(陈锡文,2014)。1986年我国农户户均耕地面积9.2亩、分散为8.4块,2008年下降为7.4亩、分散为5.7块(何秀荣,2009),1996~2011年我国经营规模在10亩以下的农户占家庭承包户总数的比重从76%上升到86%,10~30亩的农户比重从20.2%降至10.7%,2011年户均耕地面积进一步下降到5.58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等,2013)。2015年底,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农户数量仍然多达2.1亿户,占全部农户的79.6%。小规模、分散化的农业经营并未改变,土地分散化的经营格局非但没有改观,反而有恶化趋势(胡新艳等,2015a)。那么,在我国特殊的农情约束下,除了推进农地流转集中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外,实现和提升农业规模经济是否还存在其他可能的创新空间?
根据分工理论,分工和专业化是规模报酬递增得以实现的关键(杨格和贾根良,1996),规模经济的本质在于分工与专业化(贾根良,1996)。近年来,随着非农就业机会不断增多及农业生产服务市场日渐成熟,越来越多的农户出于务农机会成本的考虑会选择将农业生产环节外包,从而将农业的土地规模经营转化为服务规模经营,农业规模经济表达为分工经济(向国成和韩绍凤,2005;罗必良和李玉勤,2014;胡新艳等,2015b)。农户基于生产环节分工,通过生产环节外包,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提升农业生产经营效益的有效手段(Eliasetal.,2014;谢琳等,2014;张忠军和易中懿,2015)。其内在逻辑可以简要归纳为农户把部分生产环节剥离出去,专一从事某些环节的生产活动,同时农户转变为服务需求方,向农业经营组织或个体获取其他生产环节服务,从而提高每个环节的生产效率,通过农业生产环节分工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对此,中央提出一系列旨在促进农业社会化分工发展,提升农业生产经营效益的政策措施。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竞争充分的社会化服务”。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提到,“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完善农业服务体系,帮助农民降成本、控风险”。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支持多种类型的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开展代耕代种、联耕联种、土地托管等专业化规模化服务”,“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支撑工程,扩大政府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机制创新试点。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这些政策举措的制定与落实,可谓切中肯綮,很好地促进了农业的分工深化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在家庭经营基础上提升了农业规模经济水平。然而尽管家庭经营条件下农业分工深化推进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并提升了农业生产规模经济效益,但是农业分工社会化或农业生产服务市场化对农业规模经济的促进影响,特别是在跨社区以市场为纽带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带来农业经营模式变革的条件下,农业社会化服务规模经济是如何促进农业生产规模经济等问题,在理论上至今还没有弄清楚其内在的联系。深入探讨“双层经营”体制下农户家庭经营模式变革和社会化服务之间如何实现有机结合和协调互动,进而推进农业生产规模经济的形成和提升的问题,已然成为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1.1.2 研究问题
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是新时期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不能脱离具体的国情,这个国情就是必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双层经营”长期不变。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回答在家庭经营基础上能不能建设农业现代化的问题。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提到建设现代农业时做出了回答并提出要求:“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一要求,着眼于中国现实的国情农情和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规律,既是重大的理论创新,也是务实的实践要求,对于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向意义。坚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农户经营为主体,在不断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条件下推进农业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应是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选择。
实践表明,农业分工深化和社会化服务的发展,较好地解决了农户家庭经营的小规模和分散性问题,从而促进了农业规模经济的形成和实现。近年来,在农业分工深化尤其是农业生产环节外包乃至卷入农业产业链纵向分工社会化的基础上,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渐推进,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原来以社区为纽带的农业“双层经营”已逐渐演变为以市场为纽带的家庭经营与职业农民(或由他们组成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相结合的多元化双层经营模式。很多专家把这种市场化、跨社区、多元化双层经营体制称为市场化经营模式。观察和研究之后发现,这种以市场为纽带链接的跨社区多元化市场化经营模式找到了农户家庭经营和社会化服务之间的交集,将会有力地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进程。市场化经营模式不同于原来以社区为纽带的农业经营模式,它使农民家庭经营突破了社区边界,简化了农业规模经济形成和分享的条件,农民既能以社区内合作的方式分享内部规模经济的好处,又能以购买多元化服务的方式分享外部规模经济的好处(何秀荣,2009)。新模式蕴含着新启示,引领了新方向,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亟待探知其规律的新问题。例如,如果市场化经营模式增进了农业规模经济,那么其增进的机理是什么?或者说,市场化经营模式是如何解决原社区模式下农业生产规模不经济问题?如果说市场化经营模式简化了农业规模经济形成和分享的条件,那么是专业化分工改变了农民家庭经营实现规模经济的约束条件,实现生产(内部)规模经济和农业产业(外部)规模经济同步提高?还是促进了农户与社会化服务主体交易中的互利互补,弥补了农民家庭经营规模效益的不足?那么农户与各环节主体之间又是如何实现利益分享和交易均衡的?等等。本书选题就是基于农业分工深化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可能改变农业规模经济实现条件的基本假设,着重分析回答市场化经营模式是如何增进农业规模经济并实现规模效益分享均衡的这一科学问题,旨在研究揭示市场化经营模式对增进农业规模经济的作用机理,分析把握市场分工下农业产业或服务规模经济和农业生产规模经济互促关系及作用条件,探索认知农业多元经营主体分享规模效益的机制和条件等一般规律性问题。
1.2 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书针对我国农业经营体制模式演进的发展趋势,基于市场化经营模式有利于增进农业规模经济的基本假设展开研究,旨在分析回答市场化经营模式是如何增进农业规模经济并实现规模效益分享均衡的这一科学问题,具体目标:一是研究揭示市场化经营模式对增进农业规模经济的影响作用;二是解析揭示市场化经营模式对农业规模经济整体促进或放大的影响作用;三是探索认知农业多元经营主体通过交易促进和分享规模经济效益的过程及条件。
1.2.2 研究意义
(1)理论价值。农业双层经营体制模式的演变,没有否定家庭经营这一基础,而是演化出多元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衍生出多层次的社会化服务,形成了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农民家庭经营和多元化经营服务主体,它们经营规模大小不等,在农业产业链中位置不同,通过分工协作和市场交换均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各自的利益需要,好像农户家庭经营也没有受到规模不经济的困扰。为什么?这是一个很有理论价值的问题。回答了这个问题,可以深化对规模经济理论的认识,探寻农业土地规模经营和服务规模经营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利于把握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另外,在家庭经营基础上能不能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问题,认识上多有分歧;对如何“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问题,也存在很多有待探索的空间。如果通过研究能够找到分工改变农业规模经济实现条件和机理的合理解释,那么既可以深化对农业产业分工和协作关系的理论认知,也可为探寻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2)实践意义。我国农业农村改革正在不断深化,促进农户家庭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结合,以及扶持发展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新时期促进农业发展转型升级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然而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产业分工协作中的相互促进和利益分享等方面都还存在许多有待厘清的问题。本书研究成果可以为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改革提供一些理论思考,也可以为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提供一定的决策支持,有利于推动更加理性的实践操作。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
基于以上的研究目的,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1)农业经营制度模式市场化的演进逻辑。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通过理论分析和调查研究,探讨我国农业经营制度逐渐从以社区为纽带的双层经营模式向以市场为纽带的双层经营模式演进的历史轨迹或经验证据,分析市场模式和社区模式的联系与区别,解析我国农业经营模式演进的转换轨迹和制度逻辑,探寻牵引其演进方向的主要力量和决定因素,说明农业经营体制市场化演进方向的必然性。
(2)市场化经营模式对农业生产规模经济的促进作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基于农业规模经济的形成或来源可能与新的市场化经营模式相关联的假设,侧重从农业生产纵向环节分工深化和多元主体市场交易协作的视角,探讨市场链接的分工协作新模式对农业规模经济的增进作用。拟通过调查收集相关数据,构建相应的计量模型,观察农业生产过程或农业产业链相关环节的规模经济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市场化经营模式对农业规模经济形成的影响及机理。
(3)市场化经营模式对农业产业规模经济的综合影响。从农业产业链纵向分工(或生产环节外包)的整体性去观察,各经营主体均获得适度的规模经营收益是分工交易可持续性的必要条件。因为各主体愿意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在数量上的均衡取决于各方利益的相对均衡。那么这条产业链上生产和服务等环节的规模经济差异,是如何实现互补并提升规模收益的呢?因此,基于这一视角,拟通过调查分析和理论演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