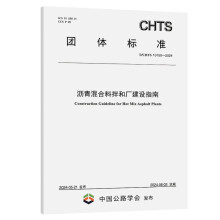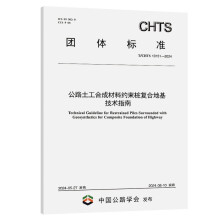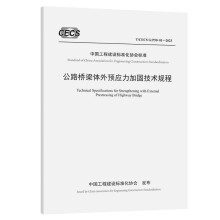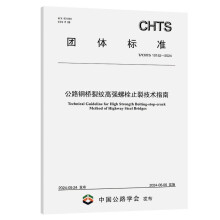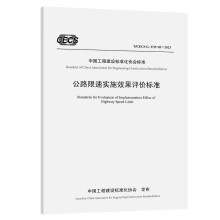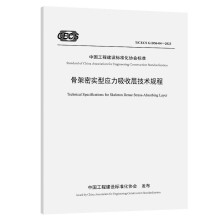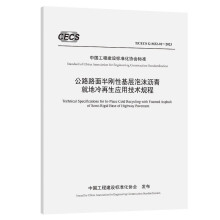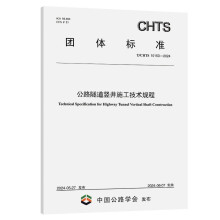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作为大城市公共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具有运能大、速度快、时间准、污染少、安全舒适、人流密集、反应迅速、系统封闭等特征,在缓解大城市交通拥堵方面具有*特优越性,适宜我国大中城市的发展模式。
面对持续快速增长的城市交通需求与日趋严峻的交通拥堵,我国提出了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多层次城市交通网络体系,许多大城市的轨道交通在近十几年经历了从单线运营时代到网络化运营时代的快速过渡。截至2020年底,中国累计有45个城市开通城轨交通运营线路7978.19km[1](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数据),2020年底中国城轨交通运营线路制式结构详见图1-1。其中,地铁6302.79km,轻轨217.60km,单轨98.50km,市域快轨805.70km,有轨电车485.70km,磁浮交通57.70km,自动旅客捷运(automated people mover,APM)系统10.20km。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和运营已迈入规模化、网络化运营时期。以南京地铁为例,截至2020年底,轨道交通运营里程为394.7km,地铁线网有10条线路、174座车站,地铁线路总长378km[2]。
图1-1 2020年底中国城轨交通运营线路制式结构
然而,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模的不断扩大,客流量急剧增加,高强度客流往往造成列车延误、乘客滞留、人群踩踏等风险。特别是城市轨道交通一般处于地下空间,具有空间封闭性、人员设备集中的特点,由于设备设施故障、人员操作失误、自然灾害突发等因素,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可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乘客伤亡,对整个城市的交通系统带来严重影响。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大客流冲击带来的列车延误、乘客滞留甚至人群踩踏等风险正威胁着轨道交通的安全运营。对于城市轨道交通事故中规模小、持续时间短、发生频率高的“小短频”事故,一般通过轨道交通运营计划调整即可快速疏散。但是运营区间中断事故等严重事故,虽然发生概率小,造成的影响却很大。众多城市轨道交通已进入网络化运营阶段,一旦发生局部运营区间中断,不仅会造成本区域的运营延误、运能降低、秩序混乱,而且会对相邻车站和线路的运营秩序带来严重冲击,在乘客从站内疏散到站外的过程中,若没有及时的疏散方案,城市地面交通将会被持续影响,发生二次事故的潜在危险急剧增加,甚至造成地面交通的瘫痪。
近年来,国内外城市轨道交通已引起多起事故[3]。例如,1999年5月,白俄罗斯地铁内由于车站客流密度过大发生踩踏事故,造成54人被踩死,多人受伤;2005年元旦,由于客流量远超预期,深圳地铁1号线暂停运营42min;2008年3 月,在北京东单地铁站5号线换乘1号线通道内,载着数百名乘客的水平电动扶梯发生故障,导致部分乘客摔倒,造成13名乘客受伤;2011年8月,南京地铁2号线一列开往油坊桥方向的列车刚离开下马坊站约200m,车厢外突然冒出火花,第三和第四节车厢上下错位近0.5m,南京地铁2号线新街口站内大量乘客滞留;2012 年10月,广州地铁1号线列车在坑口出现故障,经现场处理仍无法排除,为确保安全,调度人员组织该车在花地湾站清客,并且**时间从西朗站(现西塱站)投入备用列车调整间隔,造成沿线客流量过大,需采取客流控制与疏散措施;2015年7 月,北京地铁机场线三元桥至3号航站楼区段(下行方向)一列车车厢顶部起火冒烟,机场线全线中断运营,市区至机场方向拥堵严重;2016年11月,由于受降雪的影响,郑州地铁换乘站紫荆山站出现了人流骤增的现象,排队场面壮观如春运,从排队到坐上车需要近1h。
突发事件的频繁发生严重干扰整个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的正常运营,城市轨道交通一般处在较为封闭的地下或高架桥的空间里,具有空间封闭、人流密集、环境复杂等特点,突发中断事件极易造成大量乘客在轨道交通系统内滞留,严重时甚至引发二次事故,对乘客的生命及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同时,轨道交通因其运量大、快捷、安全、节能等特点,作为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手段之一,已逐步成为城市客运交通的骨干,轨道交通运营中断极有可能造成整个城市交通系统的崩溃。因此,及时疏运滞留客流,保障乘客正常出行,降低运营中断损失,已经成为城市轨道交通应急管理的重中之重。
为了应对网络化、常态化的城市轨道交通安全压力,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家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5〕32号),旨在建立健全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处置工作机制,科学有序高效应对突发事件[4]。当轨道交通系统本身针对运营区间中断事件启动应急预案,难以减缓或消除客流滞留与延误时,必须借助地面客运交通资源,及时调配外部运力,以替代或补充下降的轨道交通运能。在此情况下,公交车以其调度灵活方便、便于部署、运力大等优点,有必要也必须承担起为轨道交通系统提供接续功能的责任。利用地面应急接驳公交协同调度,能够达到快速响应、持续保障。这样才能确保在相对*立和固定的轨道交通系统发生突发事件后,城市不丧失主体客运服务能力,同时给轨道交通系统自身运输秩序的恢复留出必要的时空余地。
由于轨道交通与道路交通系统分属不同部门,在城市轨道交通出现运营中断的突发重大事件时,如何更好地衔接整合两种交通方式,直观高效地进行决策,使不同交通方式之间协同运转,提高应急接驳公交疏运能力和效率有重要意义。现阶段轨道交通发生区间中断后,一般做法是按照既定的疏散预案利用应急接驳公交进行疏散,缺乏轨道交通与公交协同的可视化调控系统,不能*大程度发挥公交应急接驳的作用。目前,很多城市都在积极地探索依靠信息技术改善管理模式,以信息化带动城市交通管理现代化。有效利用城市轨道交通与道路交通运行数据,发挥交通资源*大效益,建立可视化决策支持系统,实现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中断下应急接驳公交调度、运营、管理的信息化、现代化和智能化,使疏散过程可视、可控、实时,增强城市交通的应急管理和服务水平,从而有效支持有关部门的决策,推动智慧交通城市的建设。
开展城市轨道交通应急管控理论与实践研究,有助于解决以下一些问题:
(1)运营安全问题突出。很多城市本就对轨道交通重建设、轻管理,再加上急剧增长的出行需求与有限的设施通行能力矛盾日益突出,容易产生大客流,造成乘客冲突严重及设备故障率变大,诱发安全隐患。
(2)车站大客流辨识方法研究不足。现有研究主要是孤立分析一些指标对大客流进行辨识,不仅指标考虑不全,且缺乏一个系统性和整体性的量化评估标准进行大客流的辨识。
(3)安全管理水平偏低。许多国内城市大都依靠经验对大客流进行控制,不具有实时性,少有的城市构建了大客流预警系统,但也多是止于单个车站,无法对一条线路或者网络进行大客流协调动态控制。
基于以上背景,构建基于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特性分析的多准则韧性评估与优化模型,剖析基于轨道交通客流特性的大客流形成机理,甄别车站内大客流关键节点,提出基于车站客流安全状态等级的客流风险辨识与评估方法,综合车站客流控制方法、线路列车运输组织、各车站大客流预警等级等影响客流控制的重要因素,构建客流多站协同动态控制方法,以换乘时间*小化为目标构建基于列车-站点交互的网络时刻表优化模型,实现线路所有车站预警等级的整体降级和线路客流动态控制,因地制宜地设计城市轨道交通应急处置体系,提出城市轨道交通与地面公交线路应急接驳和联动疏运策略,对于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同时有助于促进对相关交通科学问题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众多专家学者对城市轨道交通已展开多年研究,其中大多聚焦于城市轨道网络化运营特性分析、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结构优化及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客流分配等研究。在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化运营中突发事件频发情形下,有关城市轨道交通的应急客流疏运、路网运输组织及公交接驳联动等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1.2.1 轨道交通供给特性分析
关于城市轨道交通供给特性的研究围绕车站服务能力与网络结构特性两个方面展开。
1. 车站服务能力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服务能力是当前城市轨道交通领域的研究热点,这是因为车站服务能力关系到车站客流组织、车站设备配备和列车运行。目前,关于车站服务能力模型的研究主要分为仿真建模与数学建模两类。
1)仿真建模
仿真模型适合于从不同角度描述车站,但很少考虑车站服务能力计算问题。Kaakai等[5]提出了一种基于混合Petri网的仿真模型,该仿真模型能够帮助交通部门执行性能评估程序;Yal?inkaya[6]基于离散事件仿真和响应面方法(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RSM)的建模方法解决了地铁规划过程中固有的平均乘客出行时间优化问题。上述研究的重点是如何对车站进行建模及评估设备的使用或服务水平(level of service,LOS),但现有的文献无法提供集成了仿真模型的车站服务能力计算方法。
2)数学建模
数学模型常常被称为分析模型,一般通过数学公式或代数表达式对地铁车站系统进行建模。大多数文献从局部的角度研究了车站服务能力的问题。《运输能力和服务质量手册》(Transit Capacity and Quality of Service Manual,TCQSM)[7]和《地铁设计规范》[8]是处理地铁站每个要素(设施)通行能力的成果,但它们并不成体系。Lam等[9]*先确定了列车停站时间与香港轻铁站拥挤情况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了列车停车延误的回归模型;Harris和Anderson[10]进行了不同列车类型上下车时间的测算;曹守华等[11]根据乘客上车时间的实地数据,分析了上车乘客的时间特征,建立了平均上车时间的分段线性数学模型;乘客到达过程是连续和稳定的,并且可以假设遵循泊松分布[12];陈绍宽等[13]通过乘客运动分析,考虑到地铁站的空间设施,提出了用于乘客疏散的基于M/G/c/c的楼梯和通道的通行能力计算模型;Xu等[14]通过概率模型,研究地铁站站台滞留乘客(到达站台的乘客将无法在相同的周期内离开(上车)并且应该等待下一个周期)。Davidich等[15]评估了等待行人的影响,并提出了一个元胞自动机模型,用于分析和预测危急情况下的等待区通行能力;Seriani和Fernández[16]分析了地铁公交换乘空间的通行能力,为智利圣地亚哥提出规划指南。Fernández等[17]证明了公共交通站台门中行人饱和流量的存在,并展示了不同条件下列车门的各种通行能力。许心越[18]分析车站服务能力的特性及影响因素,在拥挤排队网络理论基础上分别提出车站服务能力的解析和仿真分析方法,形成车站服务能力的计算分析方法体系。国内外学者侧重于研究车站的设施通行能力,没有整体上对车站服务能力的评估或计算进行研究。
2. 网络结构特性
目前,世界上的诸多大城市,如伦敦、巴黎、柏林、香港、北京等早已形成轨道交通网络,随着轨道交通的建设及发展进入网络化时期,关于轨道交通网络拓扑结构及网络复杂相关性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
在轨道交通网络特征及评估方面,曹仲明和顾保南[19]总结了城市轨道交通具备的五种基本网络结构及其相关运营特性,并分析了网络结构的优化程度及每种结构对城市结构的影响;畅明肖等[20]以2015年北京市轨道交通路网为基础,建立起轨道交通网络样本,运用复杂网络理论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北京市轨道交通网络的静态结构特性及动态加权特性;袁朋伟等[21]构建脆弱性因素辨识模型,对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脆弱性问题进行了讨论;王志强[22]等运用复杂网络的理论与方法,对轨道交通路网可靠性进行了仿真分析;Zhang等[23]分析了上海轨道交通网络的脆弱性,并且对城市轨道交通进行了网络化分析,得到了网络的个性和共性;Sun等[24]和Yang等[25]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