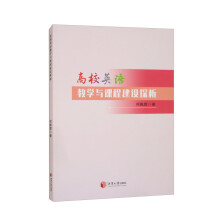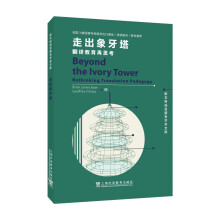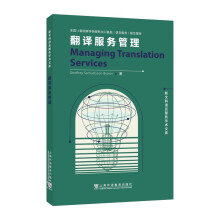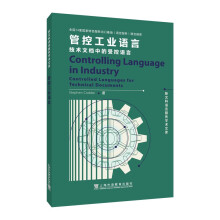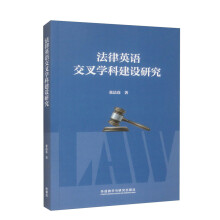三、现代悲剧意识的形成与古典感伤的现代性转变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由于受到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循环往复的历史观、忠孝节义的伦理观、内圣外王的人生观和温柔敦厚的美学观的影响,中国人普遍追求一种人与现实秩序的“和合”状态,这导致了我们缺乏西方悲剧中的那种悲剧精神。在西方的悲剧中,常常表现出一种个体与群体的对立,其悲剧意识建立在通过否定现实来实现对理想的肯定,个体出于维护和发展自我意识和个体利益,常常主动挑起和现实秩序的冲突与碰撞,而悲剧正是发生在这种碰撞所导致的毁灭性结局中。这种毁灭破坏了原有的和谐与平衡,个体也在这种注定失败的反抗中表现出一种崇高的悲剧感,西方悲剧的代表人物如俄狄浦斯、哈姆雷特、浮士德等都属于这一类“有意义的个体”。同西方悲剧中“有意义的个体”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以从属性、集体性的群体性主体来取代极端个体化的主体,以世俗化的宗法伦理来取代抽象化的绝对秩序,这种机制导致了中国文化体系中不存在西方式的悲剧精神,而只能形成一种带有相对性和调和性的悲剧意识,具体表现为:“悲剧品位的世俗性,悲剧情感的中和性,悲剧结局的圆满性”。
关于中西悲剧性的不同,王富仁先生在《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一文中有过详细的阐述。他指出所谓的“悲剧精神”,是一种“悲哀与力量的混成感觉”。,这种感觉建立在人的独立性和独立意志上,这种出于自然本能的独立性和独立意志决定了人将永远反抗宇宙的意志和大自然的威胁。但是在宇宙与自然面前,人类始终处于弱者的位置,这意味着人的反抗永远没有取得胜利的一天。然而正是在这种无望、充满悲剧性的反抗中,人的主体性力量得以显现出来,“人在这反抗中才表现着自己的独立性,表现着自己的独立意志,表现着自己主体性的力量。显而易见,这就是贯穿在悲剧中的悲剧精神”。。这种悲剧精神正是西方悲剧的精神内核所在,西方的悲剧英雄永远都在进行着无望的反抗,直至毁灭也从未妥协让步,为人类盗取火种而受到宙斯惩罚的普罗米修斯可以看作是其中最富标志性的悲剧人物。
和西方悲剧相比,中国文化中的悲剧意识同样建立在人与自然、宇宙、世界的悲剧性分裂和对立的认识中,但是和西方悲剧中明知无望却仍然反抗的悲剧精神不同,中国悲剧意识的底色是悲哀。这种悲哀决定了中国文化通过建立一种新的文化体系来调和人类悲剧性的解决方式,这套文化体系就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乐感文化。乐感文化通过抑制人的欲望和激情阻碍了悲剧精神的诞生,在这套文化体系中,儒家学派为人设计了实现自我理想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这种非个人主义的义务型人格成为中国伦理文化体系的核心所在。建立在这种文化体制中的中国悲剧意识注定了其永远无法企及西方悲剧对于人类命运的形而上思考领域,而仅仅局限于一种受动式、日常化的思维逻辑,具体表现为理想追求过程中的不得志、被遗弃或是蒙冤受屈等。总体来说,在中国古典的悲剧意识中,不存在一种超越于现存秩序或现实关系的理想,也没有对现有格局的破坏性改变,而更多表现为一种想要恢复个体与整体格局和谐关系的弥合性努力,并以此来调和日常矛盾。在中国文化中,屈原可以看作是这种悲剧意识的典型代表,“它一方面暴露了个体被整体所误解、排斥而造成的悲剧性现实,另一方面又通过个体对这一整体矢志不渝、至死无悔的忠诚和信念来进行弥合”。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