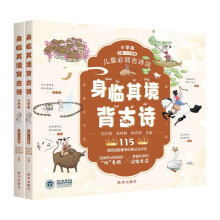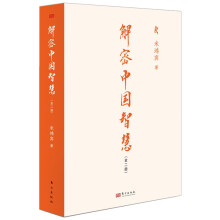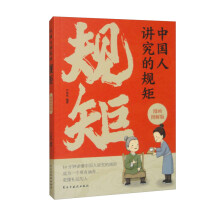《工艺文化(“日本民艺之父”“超接地气美学家”柳宗悦的工艺美论经典作,全新译本。)》:
诚然,有人表现出了一定的喜好,每次购买器物,都要细细拣选一番,辨别优劣与好恶,我们能从他们的选择中看到工艺批判的萌芽。拥有某种喜好是难能可贵的,喜好的有无,将对你的一生产生巨大的影响。可惜先进的喜好并不多,许多人的喜好停留在小而自我的范畴,因此错误的喜好屡见不鲜。
所幸已经有人迈出了一步。他们不单单拣选器物,还会细细思考如何使用它们,换句话说,他们会在日常生活中将这些器物用到极致。此举有助于让工艺更贴近生活,并为我们创造更多关注工艺的机会,如此一来,标准也会相应提高。器物的性质主要体现在其使用方式上,在这方面,日本的“茶道”尤其值得一提。茶道加深了日本人对器物的热爱,陶冶了日本人对美的情操。茶道以器物诠释了什么是美,并展示了器物的用法,其功绩不容小觑。奈何许多人将其局限在了茶室内的茶事,能彻底冲破玩赏“茶道”这一局限的人寥寥无几,更不会有茶人愿意敞开心怀,深入工艺与美的问题。
不过有另一群人在器物上倾注了他们的心血,那便是鉴赏家和收藏家。他们拥有大量的经验和智慧,众多器物的存在及其性质通过他们的鉴赏与收藏为人所知,他们自己也对此颇感自豪。但我经常感到困惑的是,他们所鉴赏的往往是古董,而非工艺。他们的第一要务是拥有,而非理解。于是便产生了一种诡异的现象: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器物与他们引以为傲的器物之间几乎全无交集,他们经常使用一些叫人不忍直视的玩意儿。
那些与美的世界关系深厚的人呢?好比在有文学、音乐抱负的人里,有没有对造型世界感兴趣的人呢?不幸的是,在今天的日本,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在我看来,对美术感兴趣的人都少得可怜,普通人在这方面的修养还有待提高。
那美术评论家呢?美术论领域颇为热闹,工艺论领域却冷冷清清。莫非他们认为,期望在工艺中发现真正的美无异于徒劳?公众对工艺的理解还很粗糙,想必这也是工艺论的匮乏所致。
翻开关于工艺的书籍,也能看到同样的匮乏。关于工艺各分支的专业著作数量可观,然而,它们是对材料和方法的科学分析,没有切入工艺本质的哲理。因此,那些书籍也很少涉及工艺的价值问题。所谓的工艺论书籍也不过是做了些分门别类,并没有深入本质问题。
那么,美学家有没有扛起这个问题呢?他们积极探讨美术,却对工艺沉默不语,哪怕提及工艺,也只会在某个章节里给它留一小块。外国的书籍在这方面同样不甚活跃。这无异于不断暗示未来的美学,要如何逃避本质问题。
工艺史家呢?我们确实能从他们挖掘出的历史细节中学到许许多多,但我们不得不直面的悲哀是,他们空有知识,却缺乏直觉。一件东西无论是美还是丑,他们往往都以同样的方式奉上赞美,这便是铁证。他们似乎难以辨别玉与石,因此其记录还算可靠,但历史观就靠不住了。归根到底,他们并没有对工艺的正确理解,特别是在谈到工艺美的时候,他们的立场往往是模棱两可的。不过对史学家而言,缺乏价值认识并不是致命的,只是基于史料的记述不能催生出工艺史观。
反倒是一些醉心于地方文化的人意识到了地方工艺的意义,因为他们深知手工艺在地方文化中的重要性。可惜他们的理解往往是思想层面的,并不契合实物,一旦牵涉到“什么样的器物才是正确的”这种具体的问题,他们给出的答案便会模糊不清。
也许我们在近代失去的一大才能就是直觉力,尤其是辨别物件美丑的能力。近代的才能似乎都集中在了知识上,因此许多人懂得抽象的“事”,却不懂得品鉴具体的“物”。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倾向于站在概念的角度观察有形之物,对工艺漠不关心,也许就是因为它太偏“物”了。美术涵盖部分概念性的内容,而工艺是更赤裸裸的“物”,所以单凭知识的力量是无法接近的。不通过观察、不靠过去就很难亲近它。在当今世界,愿意直接审视“物”的人何其少。人人都会用眼睛看东西,但很少有人有能力审视它们的内里,这一点极大地阻碍了人们对工艺的正当理解。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