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上古至五代之戏剧
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楚语》:“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中略)如此,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中略)及少皞之衰,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然则巫觋之兴,在少皞之前,盖此事与文化俱古矣。巫之事神,必用歌舞。《说文解字》(五):“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褎舞形,与工同意。”故《商书》言:“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汉书·地理志》言:“陈太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陈诗》曰:“坎其击鼓,宛邱之下,无冬无夏,治其鹭羽。”又曰:“东门之枌,宛邱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风也。郑氏《诗谱》亦云。是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商人好鬼,故伊尹独有巫风之戒。及周公制礼,礼秩百神,而定其祀典。官有常职,礼有常数,乐有常节,古之巫风稍杀。然其馀习,犹有存者:方相氏之驱疫也,大蜡之索万物也,皆是物也。故子贡观于蜡,而曰一国之人皆若狂,孔子告以张而不弛,文武不能。后人以八蜡为三代之戏礼(《东坡志林》),非过言也。
周礼既废,巫风大兴;楚越之间,其风尤盛。王逸《楚辞章句》谓:“楚国南部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俚,因为作《九歌》之曲。”古之所谓巫,楚人谓之曰灵。《东皇太一》曰:“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云中君》曰:“灵连踡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此二者,王逸皆训为巫,而他灵字则训为神。案《说文》(一):“灵,巫也。”古虽言巫而不言灵,观于屈巫之字子灵,则楚人谓巫为灵,不自战国始矣。
古之祭也必有尸。宗庙之尸,以子弟为之。至天地百神之祀, 用尸与否,虽不可考,然《晋语》载“晋祀夏郊,以董伯为尸”, 则非宗庙之祀,固亦用之。《楚辞》之灵,殆以巫而兼尸之用者也。其词谓巫曰灵,谓神亦曰灵,盖群巫之中,必有象神之衣服形貌动作者,而视为神之所冯依:故谓之曰灵,或谓之灵保。《东君》曰:“思灵保兮贤姱。”王逸《章句》,训灵为神,训保为安。余疑《楚辞》之灵保,与《诗》之神保,皆尸之异名。《诗·楚茨》云:“神保是飨。”又云:“神保是格。”又云:“鼓钟送尸,神保聿归。”《毛传》云:“保,安也。”《郑笺》亦云:“神安而飨其祭祀。”又云:“神安归者,归于天也。”然如毛、郑之说,则谓神安是飨,神安是格,神安聿归者,于辞为不文。《楚茨》一诗,郑、孔二君皆以为述绎祭宾尸之事,其礼亦与古礼《有司彻》一篇相合,则所谓神保,殆谓尸也。其曰“鼓钟送尸,神保聿归”,盖参互言之,以避复耳。知《诗》之神保为尸,则《楚辞》之灵保可知矣。至于浴兰沐芳,华衣若英,衣服之丽也;缓节安歌,竽瑟浩倡,歌舞之盛也;乘风载云之词,生别新知之语,荒淫之意也。是则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 已有存焉者矣。
巫觋之兴,虽在上皇之世,然俳优则远在其后。《列女传》云: “夏桀既弃礼义,求倡优侏儒狎徒,为奇伟之戏。”此汉人所纪,或不足信。其可信者,则晋之优施,楚之优孟,皆在春秋之世。案《说文》(八):“优,饶也;一曰倡也,又曰倡乐也。”古代之优,本以乐为职,故优施假歌舞以说里克。《史记》称优孟,亦云楚之乐人。又优之为言戏也,《左传》:“宋华弱与乐辔少相狎,长相优。”杜注: “优,调戏也。”故优人之言,无不以调戏为主。优施鸟乌之歌,优孟爱马之对,皆以微词托意,甚有谑而为虐者。《榖梁传》:“颊谷之会,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厥后秦之优旃,汉之幸倡郭舍人,其言无不以调戏为事。要之,巫与优之别:巫以乐神,而优以乐人;巫以歌舞为主,而优以调谑为主;巫以女为之,而优以男为之。至若优孟之为孙叔敖衣冠,而楚王欲以为相;优施一舞,而孔子谓其笑君;则于言语之外,其调戏亦以动作行之,与后世之优,颇复相类。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而此二者,固未可以后世戏剧视之也。
附考:古之优人,其始皆以侏儒为之,《乐记》称优侏儒。颊谷之会,孔子所诛者,《榖梁传》谓之优,而《孔子家语》、何休《公羊解诂》,均谓之侏儒。《史记·李斯列传》:“侏儒倡优之好,不列于前。”《滑稽列传》:“优旃者,秦倡侏儒也。”故其自言曰:“我虽短也,幸休居。”此实以侏儒为优之一确证也。《晋语》“侏儒扶卢”,韦昭注:“扶,缘也;卢,矛戟之柲,缘之以为戏。”此即汉寻橦之戏所由起。而优人于歌舞调戏外,且兼以竞技为事矣。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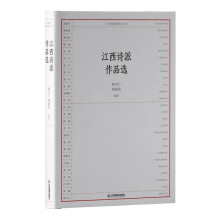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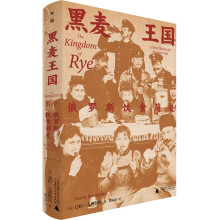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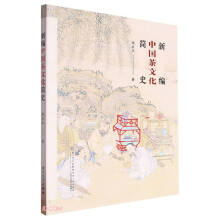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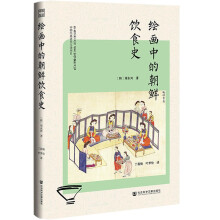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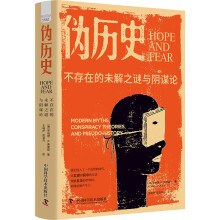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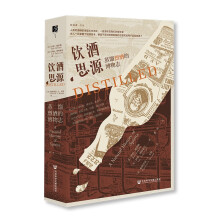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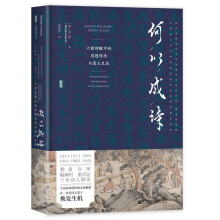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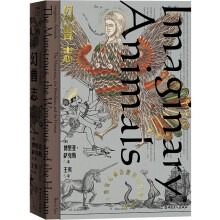
——狩野直喜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qian无古人,而且是quan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
——郭沫若
专治宋元戏曲史料,则不敢云后无来者,而前人确未有为此业者,所以能立一家言者,真是绝无依傍,全由一人孤军力战而成,此亦为先生之专门绝学,未可以其中年自弃而轻视之矣!
——吴其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