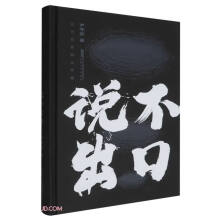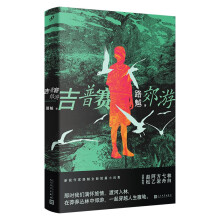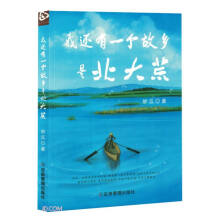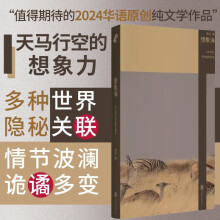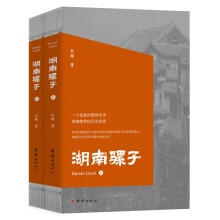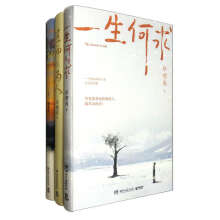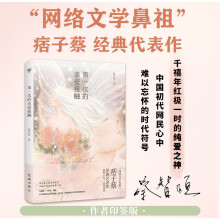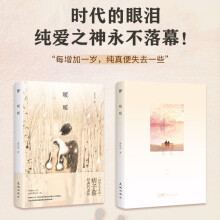第一回 清河庄草堂斗诗会 放羊倌奇缘结太公
元祐八年的寒冬,颍州城街头巷尾都在议论汴梁来的消息。太后崩逝,皇帝亲政,宣召章悖回朝为相,凡被太后及司马光旧党所废止的新法如数恢复,被贬黜流放的新党官员陆续回京任职,大有复推革新之势。从汴梁回来的人言称章宰相博学清傲,铁腕风骨,不但将朝中依附太后的迂腐奸臣尽数逐斥,还上书奏请掘开司马光、吕公著等已逝者的坟墓,劈开棺材,晾晒尸首,以示变法决心。但官家念及朝廷颜面,没有答应,令章宰相恨不能平,也令朝中曾对新法有过质疑的人心惊胆战。腊月刚到,城门便张贴了官府的告示,已废多年的青苗法果然复行,年号也改叫绍圣了。
颍州距汴梁并不遥远,我竟然才知道吕公已薨逝五年。自熙宁八年一别后,竟有二十年未再相见。如今想起,仍是心如刀绞。我感念吕公待我醇厚,无处寄托哀思,只好带了陈酿的桂花酒去西郊三十里外找孙公对饮。他早已辞官归田,每日耕读修行,六十一岁仍能登山赏景,连花甲大寿都快活得忘了。提及吕公薨逝,孙公放声痛哭,久不能停,我也跟着垂泪入盏,混着酒汤,喝起来难以下咽。孙公从内室取出吕公生前捎来的信读与我听,字字句句如浮光玄影,止不住勾起诸多往事。听到其中有一句“若你也心有愧意,可将实情告知王善,若非有托在身,不使虚瞒之也”,我问孙公:“这王善说的是我吗?”孙公道:“正是,若不是你来找我谈起吕公,这信我多半是要带进棺材的。” 第二日,我便有了南下的打算,但凡听我说到此事的人,无一不反对。世道不太平,山贼盗寇频出,举兵造反的也不在少数。而江州路途遥远,水路旱路交替,翻山越岭,不知几日才能抵达。就算平安到了江州,时隔二十年,活着已然不易,想活着遇见简直比登天还难。费二郎说:“就算找到了,你又能如何呢?”我叹然,想当初,吕公要孙公一起来瞒我,也是这样说的。
“就算找到了,他又能如何呢?”
我将田宅、店铺、买卖尽数托付给费二郎,带上盘缠,换上粗麻的衣物,挑选了几个强壮的家丁,假扮成行路的贩子,乘船沿清河南去。我深知这一路吉凶未卜,很可能无功而返,旁人甚是不解,连州府官家都登门问询。但我不以为然,浮生过半,能让我牵挂之事,也不多了。
清河水缓,船行宽阔,两岸风光绝美,正是春意盎然之季。这样的景致对我而言是再熟悉不过。日复一日,春复一年,我从清河而生,又沿清河而去。恍惚之间,三十年岁月如溪沙流光,一梦日月,一梦人间。
三十年前,我刚九岁,平日里大多数时间都是趴在蛤蟆鼓上。如今我离开颍州南下,还途经和它相遇的地方,此时它早已不在那个河湾旁,河边只剩下密集的芦苇。我趴在蛤蟆鼓上的那些年里,清河的河道尚窄,长不出许多芦苇,也听不到几声蛤蟆叫唤。
据费二郎所说,那时我虽然年幼,却天生神力。起初我还要用双肘撑起上身,眼珠子朝左右转转,望见有白色成团的影子,才能卸下力气,像一张锦被舒展开,继续伏在蛤蟆鼓上。没过几个月,我便不必如此辛苦,只需要靠耳朵和鼻子,甚至靠做梦时恍惚的念力让魂魄在周遭走一圈,便能准确知道那几只白团子在什么位置。这种本事是很少见的,至少在清河庄无人能与我媲美,当然也没有人真来与我比试,只是费二郎如此说说而已。那年他十六岁,家里理应从未有过锦被这种东西,若是说我像一张卷尸的草席摊开贴在蛤蟆鼓上,似乎要更真一些。
平日里,清河滩就是我的地盘,除了那几只白团子,还有天上的麻雀、蚊子,地上的螃蟹、田螺,草里的蜈蚣、蚂蚱,树上的蝉虫、野鼠,很少有活物到此。清河那几年雨水不多,从颍州南下的客船难得一见,焦陂的酒酿也多绕路从官道运去东京。虽说我最终也是乘船而下,但那时的我对船舶没什么兴趣,船上的人要么呕吐不止如同得了重病,要么像根柱子杵在船头一动不动。这世上一动不动的,除了吃草时突然下雨的白团子,就只有屁股底下的蛤蟆鼓了。
P1-5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