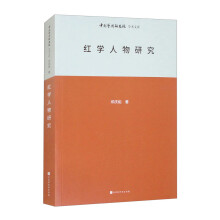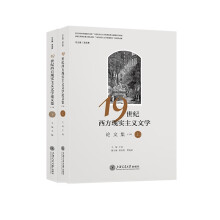《诺斯替主义影响下的哈罗德·布鲁姆诗学创造及运用研究》:
总之,诗的影响至为切要地关乎诗的创造,而且也只有基于诗的创造来论诗的影响,才使得后者对于诗歌显示出正面价值。当然,这种正面价值,归根结底由诗的影响作为否定性力量而发挥出来,并肯定性地激发了诗的创造,此适以澄明在诗的影响中存在着隐蔽的生产性。布鲁姆一再声称,无论诗人们对诗的影响承认与否,他们的诗歌创造都必然受到诗的影响的玷染,一种他所谓的“影响的焦虑”在诗人们的自我意识中或明或暗地涌动。在布鲁姆看来,诗人无一例外都是唯我主义者,或者至少处在唯我论的边缘,诗的本质在于创造,原创性对诗人而言,是他的诗歌和他作为诗人的自我得以存在的价值根基。因此,诗人对自己诗歌的原创性无论怀有多么强烈的确信,都理所应当,无可厚非。但是,诗的影响(或者换一种说法:前驱诗),往往总是让诗人对自我诗歌原创性的这种确信变得暧昧或尴尬。诗的创造不再是自明的,将诗的影响除却在诗的创造过程之外,若非批评家的盲视,则定然是诗人自我的创造性焦虑所致,而布鲁姆的洞见恰恰是,诗的创造不可避免地与诗的影响相联系,诗的影响深植于诗人自我的创造性焦虑之中。诗人为了成为自身,抑或为了重生为诗人,必须将前驱诗歌的影响转化到自己的创作之中并使之部分地成为想象性的存在。一言以蔽之,诗的创造之达成,起点在于诗人内心焦虑所固着的诗的影响,终点是诗人以各不相同的修正手段努力克服影响的焦虑。
布鲁姆坚持认为,唯有不惜与前驱展开竞争、角力到底的诗人,方能将前驱诗歌的影响占为己用,创造出自我真正原创的诗歌,他称之为强力诗人,他的影响诗学也自我标榜说仅仅关注强力诗人。他特别觉察到,当涉及强力诗人们之处,影响这个本可能是健康的东西就更通常地成了焦虑。诗人的焦虑发生在诗人意识到自我对诗的影响的占用之时,这是一种对于负债的巨大焦虑。在布鲁姆看来,强力诗人既是诗史的英雄,又是它的受害者,而焦虑之害远远大于影响之害,焦虑所产生的防御机制原本被寻求来保卫诗人免遭影响之害,却带给诗人更多的损害,让诗人自我的诗歌创造在刻意规避前驱影响的同时显得扭曲和伪诈。布鲁姆曾说:“普罗提诺喜欢称诺斯替派为‘受骗的骗子’,对我而言,这似乎也是一个对强力诗人的好描绘。”普罗提诺如是说,主要是指控他们诋毁了造物神德穆革,违背了柏拉图主义的哲学真理,是受了反宇宙的伪教条蒙骗而又到处贩卖这一伪教条的骗子。布鲁姆则对其中的观念是非撇弃不论,别具只眼地从中发现了强力诗人的形象写照,因为后者同样一面受着前驱的影响,一面却又仍大肆搬弄前驱的伎俩去篡夺影响,目的就是企图使自己成为影响。可见,诗的影响使得诗的创造在充满影响的焦虑的同时,又充满着影响的重复。在这个意义上,布鲁姆将强力诗人比拟作诺斯替派,其实他的真正意指是,强力诗人更像诺斯替派以鄙薄口吻所描述的宇宙创造主德穆革。
虽然柏拉图主义和诺斯替主义都认为德穆革所创造的宇宙实际摹仿和重复了在它之上的至高存在或神圣世界,但是二者的态度和立场截然相反。柏拉图主义赞许德穆革对理念世界的摹仿带来了一个具有理性的宇宙,一个合乎神意目的的善的宇宙,况且“宇宙”在希腊语中原本就含有秩序之义。而诺斯替主义出于对超越的上帝的绝对信仰而极力否定造物主德穆革,从而对其宇宙创造亦极尽菲薄,认为它是对普累罗麻之流溢的极其拙劣的摹仿,是恶的渊薮。在诺斯替派看来,德穆革将此摹仿自称为创造,无疑僭越甚或篡夺了上帝“创造”之名,其狂妄自大之至,定当加之以严重挞伐。然而,布鲁姆对德穆革在创造宇宙的过程中恣意挥洒狂狷之气的这种作派,却推崇备至。他有意避开了柏拉图主义与诺斯替主义针锋相对的关于宇宙善恶的争执,而特别地青睐于德穆革的宇宙创造过程及机理。柏拉图主义主张宇宙本质为善,将德穆革的宇宙创造视同理念原型的复制。诺斯替主义指斥宇宙本质为恶,将德穆革的宇宙创造看成堕落。瓦伦廷派就从来毫不区分创造与堕落,宇宙创造由于出自次级的造物神而注定是低劣的,因为造物神德穆革是神圣移涌苏菲亚误入歧途的产物,由之而来的宇宙创造必然较之更加堕落。于是,德穆革的狂妄,究其本因,实属无知:当德穆革洋洋自得于他所创造的世界,恰说明他对高于他的神圣世界一无所知,他愈自命为创造主,就愈暴露其狂妄无知。诺斯替派在普累罗麻和宇宙之间划定了高下等级秩序,从普累罗麻的流溢到宇宙的创造,后者被视为神性的退化。德穆革所创造的宇宙不仅是赝品,而且是黑暗的囚牢,将生命禁锢于无知状态。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