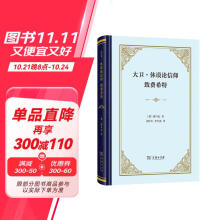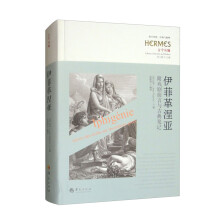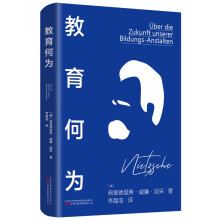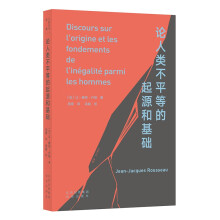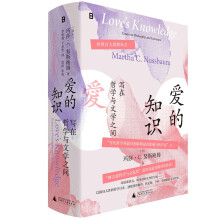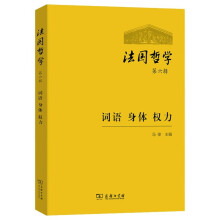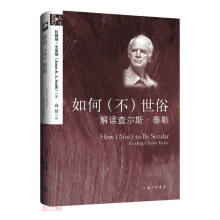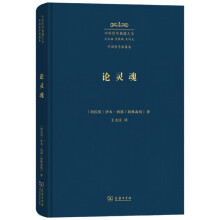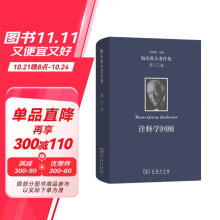《窥道路向(论“不异”)》:
费迪南德:现在,我拟对已然理解的东西做一总括:于诸宝石的多样性中,理智思想认出了某种使之归属于其种类的东西。纵使它作为种类的生成者(specificans)而被包蕴于一切宝石中,人们仍旧将之先于众多宝石而认作“不异”的相似性之形象。它使得每一颗宝石都作为宝石而存在,因而是每一颗宝石中内在的与实体性的本原;一旦离开它,宝石便无法再如其所是地持存下去了。
此一按种类进行规定的本原,将宝石可被规定为种类的存在之可能性规定为种类,并赋予此种可能性以现实的存在——当它令得宝石的存在之潜能(posse esse)经由其现实性而成为现实之存在时;当我们将混乱无序的存在之可能性阐明为,经由这规定种类的效能活动而被规定的与被形成为种类的时。而彼时,您便于个别的宝石中,将您方才以理智加以分离地观看的东西,看作可能性的现实性,因为它事实上乃是一颗宝石;正如某人对冰加以观察与思索时那样,这冰早些时候曾是潺潺的溪流,而他现在却将之看作致密与坚实的冰了。当他为此而对原因进行观察时,他会发现,这个为他以理智分离地观看的寒冷,乃是存在的某个种类,它将所有溪流的质料凝结、压制成致密与坚实的冰,以至于每条河流因为其产生着效能之原因的在场而于现实中成为了冰,只要它受其阻遏而无法继续涌流的话。纵然人们无法觅见分离于寒冷之物的寒冷,理智却将其看作那先于寒冷之物的原因,并认出,可变冷的东西于其中经由寒冷而成为了现实地寒冷的东西,而冰、霜、雹等等依可变冷之物之差异性而有的现象都是以此方式产生,并为人所觅见的。然而,由于可变冷的质料也是可变暖的,这于其它方面在自身内并不朽坏的寒冷,出于这它一旦离开便无法再于现实中被觅见的质料之缘故,便可以通过偶性而陷于朽坏的境地——就在这质料作为可变暖者而为温暖所改变时。我以为,您便是亲自向我如是宣说的。
我对于此事也有了理解:偶性是如何跟随于种类性的诸实体的。正如存在着跟随于一块冰或另一块冰的偶性,也同样存在着跟随于雪、霜、雹、水晶或某颗顽石的偶性。由这些开放与广泛的自然之杰作中,我充分清晰地觉察到,那些更深层次的偶性也并不例外,如您所简要总结的那样;亦即,那些种类性的形式与成为了实体的分离的形式都为理智思想所观察,并以如前所述的方式,于成为了种类与实体的诸多事物中被触及。然而,经由相似性,我得以由诸多感性实体中超拔到理智实体那里去。
库萨:我见到了,你是如何凭藉自然中无比合宜的譬方而清楚地阐明我的构想的,并为此感到欣悦;藉助于此种观察方式,你将洞悉一切万有。些许热量不足以像融化冰那样使得水晶消融,因为令事物冻结的寒冷战胜了被冻结之水的流动性;这全然显示出,形式是如何将质料的所有流变性置人现实中的,就像在天穹中那样,它并不为那有朽性所追随。由此,显而易见,有朽性于理智认识那里乃是不可能的;前者存在于感性事物中,后者则同相宜于变化的质料相分离。
由于在理智认识者那里,温暖并不改变理智,令它也随之变暖——就像在感性认识者那里对感官加以改变那样,那么如下这便十分显明了:理智思想并非质料性的或可变的东西;因为于理智思想中,以可变性为其特征的感性事物,乃是以理智而非感性的方式存在的。当你带着强烈的关注考虑到,理智思想先于感性而存在,并由此对于任何感官皆不可触及时,你便会于理智思想中先行觅见一切存在于感性中的东西。我说的乃是“先行”二字,亦即经由非感性的方式。正如寒冷存在于理智思想中,寒冷之物存在于感性中,而思想中的寒冷乃是先行朝向那可感之寒冷的;因为寒冷不被感知而被思想,而寒冷之物则被感知。与此相仿,那于感性领域中被觅见的,不是温暖,而是温暖之物;不是水,而是含水之物;不是火焰,而是燃着之物。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