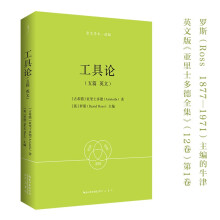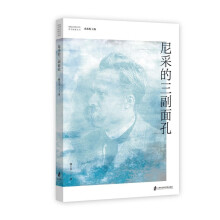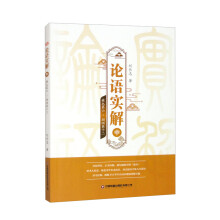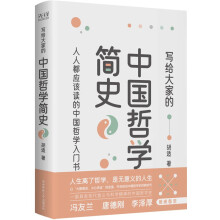近几年,书评颇有大盛之势。专门性的书评杂志、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生长起来。我经常收到的就有《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读书人报》《书屋》……据说各地新闻出版部门都有自己的书评杂志或报纸。《读书》是很早就开始阅读的,海内外知识界对它评价不错,也许今天的“书评风”,它的源头应该从《读书》开始。《读书》的畅销带动了这股“书评风”。专门的书评刊物报纸属于我喜欢翻阅的读物。
读书评是一件轻松的事。阅读书评或类似的刊物杂志,我主要是为了获得新书信息,寻找对自己有用或自己感兴趣的书籍,有时还会有更大的收获。有些书评文风清新,不落俗套,富有思想灵性,蕴含的信息量大,读起来确是一种享受,读后往往会有一种思想的冲动。说实话,我不喜欢那种制式化的书评文章,先讲某书优点,列举一二三后,蜻蜓点水似的罗列问题。好像面面俱全,给人的感觉却十分呆板。据我的观察,《读书》的书评重在推介,并不怎么批评,因而它往往成为人们了解新思想、新动态的一个窗口。在活跃的80年代和比较沉闷的90年代前五六年,它几乎是一花独放,有一大批读者,这与其发挥的独特功能有关。
写作书评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就有人情的障碍,勉强给一部书赞语,自然对作者是一种恭维,但自己又会觉得未必对得起读者;对一部有问题的书点出其“硬伤”所在,当然会立马得罪作者。其次所评著作至少应是自己的研究范围,如属自己的专长自然更好。否则,你就没有资格发言,更谈不上评论的权威性。常言道:评价要实事求是。问题就在这“实事求是”不易把握,它有主观、客观的障碍。
过去大陆的学术刊物并不怎么重视书评,这从书评所处的位置和所占的篇幅可以看出。我们每年出了那么多新书,从来未见一家学术刊物,以隆重的形式,或显赫的位置,或大量的篇幅来讨论、推介一本学术著作。如果一本书频繁出现在书评刊物、报纸上的话,很大程度是为了商业上的考虑。最近一段时期,一些学术刊物开始重视书评这种体裁,并且打破常规发表一些批评性的书评,它主要是出于对书的质量和端正学风的考虑,出于维护学术纪律和学术规范的考虑。这种做法对于戒除浮躁的学风自然有警示的作用,它能阻止最坏的景况出现。
学术书评是讨论学术的一种方式,是学人之间对话的一种便捷手段。我想,它应不同于一般书评,而又高于一般性的文化书评。一篇学术书评不仅应该准确地传达被评对象的信息,而且应能提供评论者本人的见解。后者就只有专家才能做到。
历史学的书评应该反映本学科的特殊性,接受本学科的规范制约。讲到学术规范,这也是近几年常谈论的一个话题,其中常被人提及的一点,即尊重前人、他人的相关学术成果,应该对研究起点有明确交待,对相关学术文献做周密的调查和必要的交待。其实这也只是学术常规,之所以被强调提出来,说明了当今学术界低层面重复研究的严重程度。
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衡估历史研究进步的三要求,我细细琢磨,觉得它其实也是历史研究应该遵循的三项原则(这也许是我的一孔之见),写作历史书评也应考量这三项原则。现在许多书评不仅格式一律,而且语言雷同,看不出被评对象的特色何在。与此相联的另一个问题,是评家喜下断语,而又不作细致的论证。一提一部新书就号称它“引证材料丰富”,很少见人再对所引材料的性质作分析,是直接材料还是间接材料?是习见的一般材料还是新发现的独家材料?或盛推它填补了一项空白,提出了新的见解,却缺乏对相关研究和前人论点作必要交待,更不提它进入一个新领域所需具备的条件,即作者已有的工作条件;新的论点“新”在何处,支撑新论点的依据何在?是出自作者发现的新材料,还是作者运用了新方法?应当说,学术书评与学术研究一样,它应遵循学术规范,有其特殊的技术要求。可以想象,学术书评作为一种学术批评的手段,如其自身不能深度地反映学术规范,它的功能发挥就会受到抑制。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怎么适应“批评”的国度和时代,大家不善于批评,也未养成正确对待批评的雅量。因此,在我们迈上批评初阶的过程中,我主张学术书评的语言,应力求平实,既不要溢美,也无须尖刻,以免产生学术批评以外的效果。P3-5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