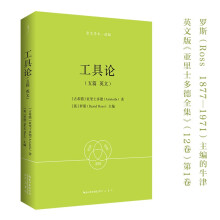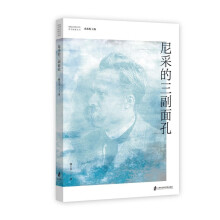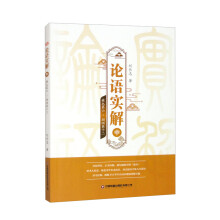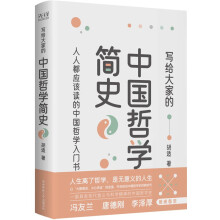《晋法家源流研究》:
第二,秦律的严酷性很可能被夸大了。有一个流行的说法:陈胜、吴广起义是由秦律“失期当斩”的酷法直接引发的。“失期当斩”的说法出自《史记·陈涉世家》中陈胜、吴广发动九百戍卒起义的演说:“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秦律有无“失期当斩”的规定,今已无考,但查《睡虎地秦墓竹简》“徭律”可知:“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可见,为朝廷征发徭役,如果误期,主要是罚款。同时又有:“水雨,除兴。”如果遇到大雨耽误行期的情形,则免除征发。说明秦律对大雨失期的规定是免除责任的,从中可以窥见秦律还是相当有理性的。虽然这是关于服徭役的规定,对于服兵役也许严格一些,但以此为参照,也不至于“失期当斩”。退一步讲,即使秦律有“失期当斩”的规定,也应该是针对故意失期的情形;而对于大雨失期这种不可抗力的原因,问斩的可能性应该很小。所以,陈胜在上述动员戍卒起义的演说中也说:“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陈胜的话表明,遇雨失期不一定问斩,但戍边而死的可能性则较大。陈胜、吴广还设计杀了带兵的两尉,这就相当于逼迫大家造反了。因此,戍卒显然不愿意为朝廷卖命,而在陈胜的大力鼓动下起义。再考虑到陈胜年轻时即有成为王侯将相的“鸿鹄之志”,不满足于像“燕雀”一样躬耕陇亩,因此大泽乡起义可以说是陈胜借机发动的,与秦律的严酷性关系不是很大。刘邦的起事与陈胜大同小异,一半是不愿服徭役,一半是受陈胜起义的影响。各地旧贵族复辟势力纷纷响应,试图重新恢复旧诸侯的分封制,对抗秦的郡县制帝国。旧贵族的代表项羽在灭秦后,并没有实行帝制,反而大搞分封制,刘邦也被封王,所以项羽最终将天下一统的历史使命拱手让给了刘邦。可见,秦律的严酷性并不是造成秦亡的唯一原因。
第三,法律的严酷性往往源于专制政体。秦国失败不是因为推行的法治,而是因为其尊君集权的绝对权力体制。秦国法治的价值导向追求富国强兵,尊君抑民,缺少道德关怀,激起社会普遍的不满。亚里士多德说过,法治的两个要素是普遍的遵守加上良好的法律。法家主张“法自君出”,而良法的制定显然不能依靠独断的君主,反而要求限制君主的独断,使君主也服从普遍性的立法权。晋秦法家过分强调民众服从君主制定的法律,且不问法律本身的善恶与否,也不主张对君主的权力加以限制,犯了西方实证法学“恶法亦法”的错误。而恶法的源头正是专制的权力,所以说君主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是秦亡的根本原因。
因此,不能因秦亡而否定法治本身。秦亡于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然而,汉儒却将秦亡教训问题带偏了,归结为不施仁政。为了建立自己的统治,儒家给法家贴上“暴政”的标签,将法治与暴政画上等号,得出秦亡于法治的结论,借以巧妙地否定了法家和法治,从而弃法治而主德治,使中国历史走上了儒家人治、德治的道路。不同于法治发展的最高层次就是治君,德治在根本上是治不了君的,儒家试图以道德约束来控制君权,然而这种自律性约束无法防范暴君的出现,因此中国历史无可避免地走进了一治一乱的历史周期律。对此,贾谊和汉儒难辞其咎。
秦亡于暴政,而非法治,总结秦亡教训的正确思路应该是如何健全法制,防止极权暴政,回到形式法治,核心是建立起君权约束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君主专制集权政体才是暴政的潜在源头,因为对民众权益的最大威胁不在于严法,而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和权力的滥用。推行法治不是依靠加强君主权力,而是要约束君主权力。要从秦亡中吸取教训,采取儒家的德治不过是治标,根本途径还是建立起约束权力的政体机制,这才是治本。法治的要义是约束权力,这也是商鞅之问的答案。商鞅法治的大方向是对的,只是过于严酷;韩非法治过多掺人权治的因素,走向专制人治。如果沿着商鞅形式法治的思路探索下去,就会找到“必行之法”,中国古代法治可能会围绕着改良政体,走向君主立宪的道路。可惜法家法治随秦亡而陪葬了,中国古代的法治事业戛然而止。贾谊没有看到秦亡于专制权治的深层次原因,只是指责秦法严酷这一浅层原因,进而否定法治,要求以德治代替法治,而未认识到专制权力的危害性。圣人德治只是儒家的美好理想,无法从根本上约束暴君,造成“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局面,同时抑制了民族的制度创新能力,因此中国历史进入循环停滞阶段,没能跳出王朝兴替的历史周期律。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