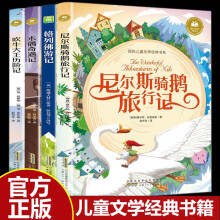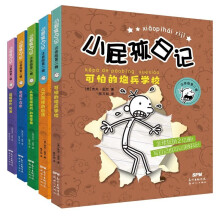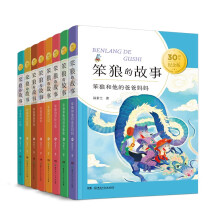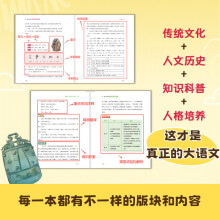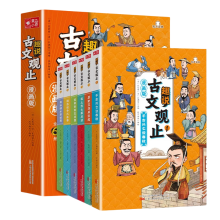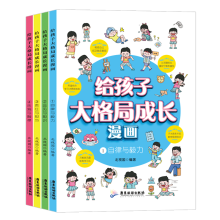山村小学
我们村有一两百户人家,都是吴姓。我小时候,村里最堂皇最神圣的建筑,就是供奉着祖宗牌位和“天地国亲师位”的祠堂了。祠堂铜环大门的门额上,高悬着一块黑底金字的大匾——“吴氏宗祠”。这四个行书大字金晃晃的,苍劲有力,那字的结构,钩点撇捺的沙笔中仿佛挟带着风声。
这座堂皇的祠堂,也是村里的学堂。喜气洋洋的“龙沿村小学”的牌子,就挂在大门旁的门枋上。正对大门的旗杆上,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地欢笑着,看着一群高高矮矮、男男女女的学童跑出跑进,用读书声和笑骂吵闹声,驱散这里曾经有过的神秘和神圣,使它成为一所真正的山村小学。
大门外有一块作为学校标志的操场,周围都是田地、菜园。菜园一角的一口老井,用青石砌成的井栏上,布满深深的绳印,表明它的古老。向日葵金黄的轮盘,沙沙作响的苞谷的绿叶,往往会高过围墙,探头探脑地向正在读书写字的小学生张望。菜园里的南瓜藤,会沿墙爬上学校的房顶,在蜜蜂的嗡嗡声中喜气洋洋地开花结瓜。到摇响铜铃下第一堂课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阳光下,菜园里的蔬菜,田地里的庄稼,因为种类的不同而显出各自生命的色泽,嫩黄、粉绿、娇红,一片水光莹莹。
忽然,学校镶着铜环的大门开了,一群小学生飞了出来,借着草叶上的露水,都来磨铜墨盒了!墨盒有大有小,有方有圆,还有长形的、椭圆的。盒盖上的画面则有“渔翁垂钓”“岁寒三友”“深山古寺”等。紫铜的暗红稳重,白铜的银色清幽,黄铜的灿烂夺目。同学们在草埂上磨着,擦着,比试着,争论着,嬉笑着,吵闹着。一个个锃明灿亮的铜墨盒,映着天光,映着草色,映着同学们的笑脸。湿润鲜亮的早晨,是我们山村小学最快乐的时刻!
接着,李老师的大口哨吹响了!同学们把铜墨盒收起来,按高矮顺序排好队,在李老师的带领下做课间操,或者听着李老师的口令,“一二一,一二一,一一,一二一”地走正步,要不,就是哗哗哗地跑步;直到李老师的哨子曜的一声叫停,同学们才哗啦一下解散,吵吵闹闹地走进教室,继续上课。
我就是在这所小学——可爱的山村小学开蒙识字,学会写自己的名字的。
我们二三十个学生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就只有一个老师,同在一间作为教室的大殿里上课。李老师年纪轻轻的,高个子,上衣口袋里别着一支水笔,脖子上挂一只象征权威的锃亮的大哨子。当四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在做四则运算题的时候,李老师就教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读“开学了,开学了,我们天天去上学”。二、三年级的学生呢,这时候可能是写大楷,也可能开始钻桌子、吵架,千些五花八门捣乱的小把戏,直到李老师腾出沾着粉笔灰的手来收拾他们。
李老师的巴掌很大,挨上一巴掌,可不是闹着玩的!李老师管教学生最拿手、最方便也最具权威性的,就是他的大巴掌。他的巴掌挥动起来,能扬起一阵风。
除了挥动巴掌,李老师就只会在罚站上玩点儿花样。比如站板凳,特别是女同学胆子小,他偏让她们抖手抖脚地站在高板凳上;又比如喊一声“站直了”,就会有一碗冷水放在头上,让你顶着,一动也不敢动。最有趣的是帮他生火。那往往是快放学了,他找个借口罚学生去帮他生火做饭。那学生走到门口,回头做个鬼脸,得意劲儿倒仿佛是受到了莫大的奖励。不一会儿,一股火烟味从隔壁的厢房透进教室,同学们的肚子也就开始咕咕叫了。
一天,就在李老师说“下课”的时候,大石宝悄悄告诉我,李老师叫“李继果”,是老东山那边的人,初级师范毕业后,分到我们村来教书。我问大石宝怎么知道的,大石宝举举他的雕刀,噫,原来他还给李老师刻过图章呢!
李老师书教得好,据说好几个村都来要他,我们村抵死不放。李老师也喜欢我们龙沿村,不愿离开我们龙沿村。他带着我们向米丘林学习,搞各种好玩的“科学实验”:比如,在洋芋苗或者瓜苗上嫁接番茄,在梨树上嫁接苹果……我们村那时没有苹果树,李老师教我们用花红树代替。当然一样也没有嫁接成功,大人们不敢说李老师,倒是把我们骂得贼死。我们呢,却是深信不疑,相信米丘林是对的,我们李老师也是对的!
每隔个把月,李老师就带我们上山砍柴。本来村里说,学校烧开水,还有老师煮饭、烧水的柴火都由村里提供;李老师用毛主席的话教导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带我们去砍柴,除了劳动锻炼,还是开展一种互相帮助的集体活动。李老师布置我们带镰刀、砍刀、背箩和绳子,还有晌午……一听说“晌午”,我们都欢呼起来,一片叫的都是“带洋芋”。李老师笑了,他和我们一样喜欢吃烧洋芋。在同学们吼吼叫叫的时候,我见大石宝总是一脸平静或者说漠然地看着窗外。这样的活动,他因为拄着双拐,所以不便参加。但他还是按时来到学校,写字,或者雕刻个什么物件。他给自己安排功课。
我们村后的山上长满了树,最多的是松树、麻栗果树。松树的种类多,常见的有科松、赤松、罗汉松、黑松等。科松结松苞,松苞成熟了,里面的松子很好吃。不过我们砍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