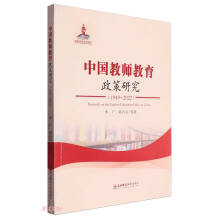中国的传统教育在某些方面跟鼎盛时期雅典的教育非常相似。雅典男童须一字不落地背诵荷马史诗朝,中国男童也类似地要对儒家经典烂熟于心。雅典人学到的敬神方式是这样的:由外部仪式组成,并且不会给知识思考设置障碍。同样,中国人习得了跟祖先崇拜相关的特定礼仪,但绝不意味着必须接受那些礼仪所暗含的信仰。温文尔雅的怀疑主义是有识之士应有的态度:凡事都可以讨论,但贸然下定论的做法难登大雅之堂。各种观点应该是可以在用餐时心平气和交流的东西,而非供人逞胜斗嘴。卡莱尔称柏拉图是“一位高贵的雅典绅士,至死也不改神定气闲”。这种“至死不改神定气闲”的风范也可以在中国圣贤身上看到,但在基督教文明所产生的圣贤身上通常难觅其踪影,除非像歌德那样深受希腊精神熏陶的人。雅典人和中国人一样都愿意享受人生,而且拥有一种因细腻美感而得到升华的享乐观。
然而,这两种文明也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源于这一事实:总体而言,希腊人精力充沛而中国人慵懒散漫。希腊人将其精力投入艺术、科学和战争,并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空前成就。希腊人的精力实际地转化成了政治抱负和爱国精神:当一位政治家被推翻,他会率领一批亡命徒去攻打他的家乡城市。而当一名中国官员遭到贬黜,则会退隐山林,写写田园诗,聊以自娱。由此,希腊文明毁于己手,而中国文明只能亡于外敌。不过,这些差异似乎不能完全归因于教育,因为儒教在日本从未产生这种作为中国士大夫特色的闲适而文雅的怀疑论,只有京都贵族例外,他们毕竟属于圣日耳曼区人。
中国的教育造就安定和艺术,却未能孕育进步或科学。这也许是怀疑论顺理成章的结果。炽热的信念带来的要么是进步,要么是灾难,但不会是安定。科学即使在攻击传统信念时,也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它在一种文人怀疑论的氛围里很难昌盛。在一个被各种现代发明所统一的好斗的世界里,活力是民族自保所必需的。而且没有科学,民主也不可能:中国文明只为少数受过教育的人所享有,希腊文明则基于奴隶制。由于这些原因,中国的传统教育不适合现代社会,并且已经被中国人自己所抛弃。某些方面跟中国士大夫相似的18世纪有教养的绅士,也由于相同原因而销声匿迹了。
所有大国都有一个突出的倾向,即以国家强盛为教育的至高目的,现代日本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日本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这样的公民:既充满为国家献身的热情,又通过知识的学习成为国之栋梁。对日本为达到这种双重目的所采取的手段,我无法大加赞赏。自佩里将军的舰队抵达以降,日本人陷入了难以自保的境地;除非我们认为自保本身有罪,日本人在这上面的成功证明他们的方法是有效的。但是他们的教育方法只有在绝境中才具有正当性,任何未处于紧迫危险中的民族使用这些方法都应受到谴责。连大学教授都绝不能提出非议的神道教,其包含的历史跟《创世记》一样可疑;在日本的神学专制面前,达顿审判不值一提。同样还有伦理专制:民族主义、孝道、天皇崇拜等都不容置疑,以致许多方面的进步都近乎不可能。这种刚性体制的最大危险在于引发革命,因为革命是其进步的唯一途径。这种危险虽非近在眼前,却真实存在,并且很大程度上是由教育体制引起的。
由此我们看到,现代日本的弊病跟古代中国的弊病恰好相反。中国的文人雅士过分怀疑和懒散,而日本教育的产物又显得太过独断和奋发。遵从怀疑主义和遵从教条主义都不是教育应有的结果。教育应该产生这样的信念:虽然困难,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获得的;任何时代被视为知识的东西,都或多或少有错误的地方,通过谨慎和勤勉可以纠正这些错误。当我们依据信念而行动,应该警惕因小过而铸成大错;尽管如此,我们的行动还是必须基于信念。这种心态颇难做到:它需要高度的理智修养,并且情感不应衰萎。不过,虽不易也,非不能也;事实上这就是科学的心态。跟其他美好事物一样,知识的获取固然困难,但并非不可能;教条主义者忘记了困难,而怀疑主义者否认了可能。两者都是错的,他们的谬误一旦蔓延,就会给社会带来祸患。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