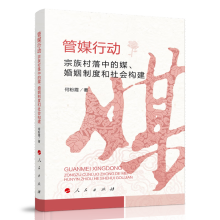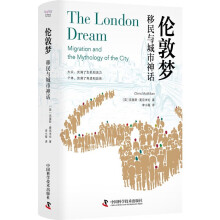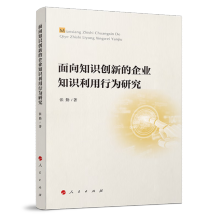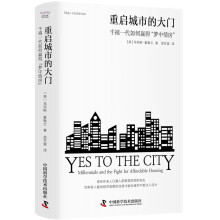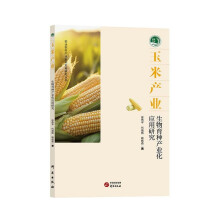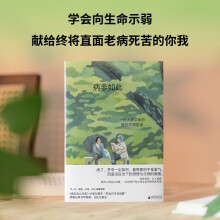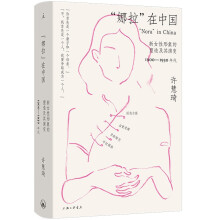《西南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审美研究》:
以真为美的审美意识体现在苗族个体的生活方式上,这和苗族的族群生活方式具有同一性的特点。苗族长期受到恶劣的自然环境威胁和外族统治的压力,苗族深知唯有将个体生命和整个族群的利益视为一体,才有战胜困难、摆脱危机的希望。苗族在生命存在中,选择了最为本真的方式。苗族的婚姻观念体现了对生命的传承模式,体现了生命的自然意义。
例如,向启军在散文《远徙的魂》中处处体现了苗族群体在迁徙途中的集体意识。文中描写道:一只只独木舟、一只只水筏上载着紧张激动的人群,一个民族在渡河,度过死亡、渡向彼岸、渡向生存。波涛滚滚,敌人强大,苗族也不会屈服。即使被打败了,这个民族也不会毁灭。迁徙的队伍哼着忧伤的歌,但不会绝望,队伍越来越壮大强健。夜深了,妇女们没有睡,为男人老人小孩编织着草鞋,缝补着衣服,等待天亮时再次启程。
杨嘉莉在小说《梦归家园——一部苗族家庭回忆录》中写到了“我”的家人和其他苗族人在迁徙途中。苗族人分工合作,男人们在四周巡逻,守护家人。女人们陪着孩子,做着饭。男人们则逃进丛林,继续寻找走散的家人。苗族人期待着有一天大家能重逢。书中描写道,苗族的白苗和绿苗原本并不来往,但在艰难的情形下,他们相互帮助,相互安慰,共同生活。他们感觉自己都是苗族人,有着共同经历的民族,尽管他们说话的语调不同,一种圆润悦耳,一种明快简洁,但他们都明白,不同的苗族方言都是在共同的境遇下产生的,在丛林中,他们明白了他们得不到其他民族的帮助,苗族人之间可以互相帮助,已经住下的苗族难民给新来的苗族人一些毯子、塑料和竹子。在苗族人面临共同的困境时,他们尝试将不同支系间的距离拉近,学会了团结一致,共渡难关。
在王伯理的诗歌《我知道的亡者》中,他将蚂蚁拯救同伴和苗族拯救同族相比。王伯理在诗中提道,蚂蚁有着吃掉同类的天性,不过,在危急时刻,它们就像人类一样把将死或已死的同伴带走。此外,王伯理将蚂蚁觅食的情景和战争的场景相联系。诗中提道,战争的场景显现在“我”的脑海中,正午,丛林,无家可归的苗人,苗人四处藏匿,他们为了寻觅食物而遭到敌人的袭击。尽管他们奄奄一息,同伴仍对他们不离不弃,将他们从炮火硝烟中带离。和其他迁徙苗族一样,王伯理也经历了战争、家人分离、食不果腹等痛苦。在写给战场上兄弟的书信中,王伯理提道,“我”为自己的逃离感到忏悔。“我”仅能用文字祈求祖先拯救你的灵魂。童年,“我们”一起骑着神圣的水牛,相互嬉戏玩耍。“我”多么希望风儿能将你带到“我”的身旁。
苗族人在危难时刻,都以民族整体的安危为己任,每个人都在为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苗族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团结的民族,男女老少分工合作,共同克服困难,战胜危机,才换取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这种集体主义精神是苗族人以真为美审美意识的体现,是苗族人对民族最真挚的情感表达,是每个苗族个体对民族尊严最真心的维护。
在“五缘文化”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苗族的血缘文化,其核心内容则是苗族的婚姻文化。苗族婚姻是扩大族群力量的有效方式,对族群成员的婚嫁也有一定的限制和要求。苗族人一般不允许和外族通婚,目的是保障族群关系的纯洁性,避免族群文化受到外界的干扰和同化,并确保本族血缘的纯洁、种族的纯正和文化的传承。苗族婚姻制度的第二个原则是同姓不婚配。同姓主要指较近血缘关系的族人不允许结婚,目的在于保障生命延续的质量。苗族的婚姻文化是对生命自然属性的体现。在满足苗族婚姻制度要求的前提下,苗族的婚姻选择具有很大的自由度。苗族的婚姻制度对增强族群的内部凝聚力、促进民族的繁荣昌盛大有益处,苗族的婚姻观也体现了苗族婚配方式的民族意义和社会意义。
韩棕树的小说《苗山悲歌》讲述了石三哥和一位施姓美女在对山歌的过程中相互产生了好感,并通过对歌得知对方姓名的故事。美女叫施黛妮,在歌声中石三哥把“施”理解成了“石”,苗族规定同姓人不能结婚,这是苗族人千百年来的规定,犹如神圣的法律一般,谁也不敢违背,因此这段姻缘以夭折告终。
……
展开